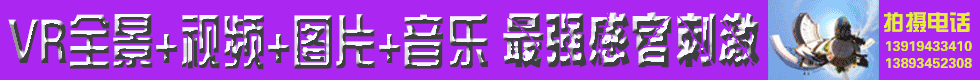字結(jié)構(gòu)是由平行和交叉的不同組合所組成的,這兩種關(guān)系是字結(jié)構(gòu)所有關(guān)系的構(gòu)成總和。換言之,平行并列線條的寬窄變化和交叉角度變化構(gòu)成了字形千差萬別的變化,任何兩條平行線條的拉近和拉遠,兩根交叉線條銳角的變化都會形成新的字形。楷書字結(jié)構(gòu)是規(guī)整的,線條之間的平行和角度關(guān)系是固化的,而行書、草書則是千變?nèi)f化的,一人一種字形。事實上,每個人的寫作習(xí)慣對線條的應(yīng)用是對幾何體的感知所決定的,這涉及到了空間感的問題,也涉及美學(xué)問題。比如“又”,三根線交叉形成4個三角形,線交叉改變1度,4個三角形就會發(fā)生變化。
線條在分隔字結(jié)構(gòu)的同時,也造就了章法。行與行之間形成了新的幾何關(guān)系,每個行距就像一個長方形的體積上伸出了各種不同的幾何體,這些幾何體在分隔字與字空間的同時,又形成和下一行的聯(lián)動關(guān)系。這些空間就像是迷宮,又像是軍隊列陣,動靜有序,排列無序。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線條邊緣的變化由于紙和墨、筆三者的關(guān)系,筆在控制墨的流向時,會在邊緣部分出現(xiàn)氤暈,墨在紙上的散開,一方面是墨流體本身的不可抗拒性,另一方面則是書者的控制能力,兩者會在線條邊緣形成不同的更為復(fù)雜的幾何體形。如果說字結(jié)構(gòu)和章法是宏觀分析的話,那么線條邊緣的則是微觀分析。恰恰是線條邊緣的變化構(gòu)成了字結(jié)構(gòu)和章法的意想不到的藝術(shù)效果。

“九”字橫鉤沒有向上,而向下鉤的轉(zhuǎn)折處筆鋒的停留。“月”字豎鉤鉤起時,筆鋒有過短暫停留,使墨色散開,使得一橫起筆如柳葉,秀美端莊,落筆筆肚按下,略作停留。這些線條內(nèi)部的不同運動使這一橫充滿了力量和體積感, “五”字省去了一橫,筆畫形成了一個末三角。“月”字通過兩點的位置,使字內(nèi)空間宛如一潭泉水,憨態(tài)可掬,厚重古雅,表現(xiàn)了良好的空間感和對筆法的控制。
中國書法發(fā)展過程中擁有完備的理論技法體系?髵,書法是在書法理論的指導(dǎo)下不斷變異的。衛(wèi)恒的《四體書勢》、王羲之的《自論書》和《筆勢論十二章并序》,從書法的起源、字體形成、筆法、章法,以及書法與個人的情感等多方面加以論述。綜觀魏晉書法理論,基本上是以玄學(xué)為基礎(chǔ)而產(chǎn)生的,由于玄學(xué)本身的局限性,使得這些書法理論有一定的局限性。書法是抽象的藝術(shù),卻是以具象的線條為基礎(chǔ)的。書法線條質(zhì)量主要來自于對筆鋒的控制。
如何控制?控制之難在于使轉(zhuǎn)、提按過程中筆鋒的調(diào)換能力,說白了即:使轉(zhuǎn)提按是為了字形結(jié)構(gòu)和章法需要,也是筆毫鋒面的赱向過程,其難度在于同時進行,往往是顧此失彼。調(diào)鋒核心是讓筆毫著紙面均勻平衡,即保證做到每個毫毛接觸紙面并與其產(chǎn)生磨擦,所謂萬毫齊發(fā)是也。用筆力量的角度一一力量來自于那塊肌肉,不同肌肉產(chǎn)生的力傳之筆尖使筆毫的著紙面不同並形成異樣的磨擦,仿佛無形的手在指揮筆鋒在運動一樣。這個過程的微妙感覺不可言傳。臨帖就是去找這種筆法寫作狀態(tài)和運毛筆的內(nèi)在規(guī)律。對筆控制力更多來自于腕與肘間的下部扭力,而非上部的平衡傳導(dǎo)力。這與每個人的肌肉傳導(dǎo)力和心理暗示有關(guān),也許有人更多來自于上部,但是無論所部你得有這種思維意識去體驗不一樣部位的力量對筆鋒產(chǎn)生的變化帶來的線條質(zhì)量。注意這里的三層關(guān)系,1力源,2作用于筆鋒(這個過程看不見),3墨線不同變化。找鋒是讓力量作用于筆鋒的那個位置,即筆觸接觸紙的那個橫斷面才是力的支點,是那個橫斷面而絕非整個筆身或筆尖,那個橫斷面就是決定墨線粗細變化的那個部位吧。筆毫的控制點就在這個位上,這時你會感到筆身是硬的和筆桿聯(lián)在一起,而這個部位以下筆頭部分是軟的,綿的,自由的形成力的迴旋區(qū)和墨的沉淀區(qū),書者會有一種意志與運筆隨心所欲的快意,一種駕馭自如的感覺。因此,需要用生理學(xué)、力學(xué)、心理學(xué)等現(xiàn)代科學(xué)展開對書法的研究,這是當(dāng)今書法必須面對的問題。 (責(zé)任編輯:李勤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