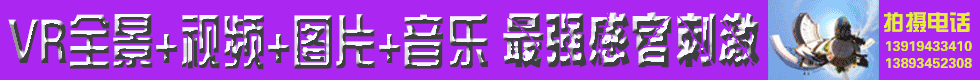大西北網(wǎng)7月13日訊,7月11日蘭州氣溫達(dá)到33度,8時(shí)30分許,三三兩兩的人們開始走進(jìn)蘭州市圖書館。大門左右兩側(cè)的電子顯示屏上,不時(shí)用紅字滾動(dòng)播出:“楊重琦樓蘭殘紙書法研究公益講座”的字目。“樓蘭殘紙”是什么?它和書法有什么聯(lián)系?新穎的講座不僅吸引了眾多的書法愛好者,同時(shí)也吸引了不少行人步入市圖書館。
記者放眼望去聽眾中既有白發(fā)蒼蒼的老者,也有稚氣未脫的少年。他們中有互相熟識(shí)的,但絕大部分人是第一次見面。然而,共同的愛好和興趣讓他們很快打消了生疏感,王羲之、顏真卿、柳公權(quán)、歐陽詢、趙孟俯、于右任、趙樸初、黎泉,從古代的書法家到近代以及甘肅的書法家,人們各抒己見談興十足,現(xiàn)場儼然成了書法沙龍。這里沒有年齡、職業(yè)的區(qū)分,只有對書法的探討和青睞。
在濃郁書法的氛圍中,身著短衫,戴著眼鏡的楊重琦先生走上講壇,“感謝大家在這么熱的天來到市圖書館,現(xiàn)在我就樓蘭殘紙發(fā)現(xiàn)的意義,以及它對書法的影響談一談自己的看法。”簡短的兩句話拉開了講座的序幕,頓時(shí)報(bào)告廳內(nèi)鴉雀無聲,只回響著楊重騎抑揚(yáng)頓挫的講座聲音。“樓蘭文書殘紙專指在樓蘭發(fā)現(xiàn)的墨書的殘紙和木簡。文書殘紙有明確紀(jì)事的最早上限是三國魏齊王曹芳嘉平四(252年),下限最晚建安十八年(330年)。由于沙漠干燥的得天獨(dú)厚的原因,雖在地下埋了將近2000年,仍然是黑色如新,宛如昨天書寫的一樣保真。”“真不簡單。”“簡直是一個(gè)傳奇。”聽眾中有人發(fā)出唏噓聲。
“樓蘭文書殘紙先后分5次發(fā)掘整理,歷時(shí)百年。第一次發(fā)掘是1901年3月,瑞典考古專家斯文·赫定探險(xiǎn)隊(duì)發(fā)現(xiàn)了樓蘭古國遺址。第一次發(fā)掘出樓蘭文書,讓世人為之震驚。其中木簡121支,殘紙36片。第二次發(fā)掘時(shí)間是1906年12月,美國人斯坦因?qū)翘m古國遺址發(fā)掘木簡166枚,殘紙36片,由大英博物館收藏。第三次發(fā)掘是1909年3月,日本青年探險(xiǎn)者橘瑞超走進(jìn)樓蘭古國遺址,挖掘出木簡4枚,殘紙5片,現(xiàn)藏于日本東京龍谷大學(xué)圖書館、第四次發(fā)掘是1914年2月,斯坦因走進(jìn)樓蘭王國遺址,發(fā)掘出木簡59支,殘紙44片。第五次發(fā)掘在1980年4月,新疆考古隊(duì)研究員候燦對樓蘭王國進(jìn)行調(diào)查時(shí),發(fā)掘出木簡63支,殘紙2片,這是唯一一次由中國考古學(xué)者自行組織考察的調(diào)查活動(dòng)。1999年候燦、楊代欣合著《樓蘭漢文簡紙文書集成》一書,該書首次從中國文學(xué)史和中國書法史的角度,對樓蘭殘紙文書作了系統(tǒng)地、深刻地考察和研究。”
樓蘭國是紀(jì)元前后古絲綢之路上的一個(gè)國家,樓蘭古城是樓蘭國的首都,是古絲綢之路上一個(gè)重要的“節(jié)點(diǎn)”城市,那時(shí),樓蘭和敦煌一樣聞名。可后來風(fēng)沙摧毀了這個(gè)曾經(jīng)繁榮的商賈古城,但風(fēng)沙在侵蝕的同時(shí),也保存了它的存在。“樓蘭國原來這樣有名,樓蘭殘紙發(fā)現(xiàn)竟有如此之多的故事。”人們悄聲感嘆道。
“樓蘭殘紙”是中國最早寫在紙上的書法,它比王羲之的蘭亭序集還早了四五十年。“‘樓蘭殘紙’”對研究中國書法初始化狀態(tài)及對書法的影響和傳承關(guān)系。為各時(shí)代的文化研究和窺探書法發(fā)展內(nèi)在規(guī)律提供了依據(jù)。”之后,楊重琦先生在課件上展示和對比,對其歷時(shí)十年現(xiàn)存資料的研究和實(shí)踐,對“樓蘭殘紙”進(jìn)行了理性分析,并揭示導(dǎo)致書體發(fā)生變化的重要內(nèi)在因素,以及探究書法傳承的核心基因。楊重琦先生在講座中妙語連珠,不時(shí)穿插運(yùn)用歷史故事和自己練習(xí)書法的心得體會(huì),與聽眾交流溝通。
從9時(shí)30分到11時(shí)40分左右,整整兩個(gè)多小時(shí)楊重琦先生一口氣講完了樓蘭殘紙書法研究的講座。講座期間人們專心致志,現(xiàn)場不時(shí)傳出“沙沙”用筆記錄的聲音,楊重琦先生結(jié)束講座后,十幾名聽眾圍住楊重琦先生,和他零距離進(jìn)行互動(dòng)。
退休水利工程師喻得安告訴記者,他是一名書法愛好者,楊重琦先生的樓蘭殘紙書法研究講座讓人耳目一新,這使他對中國傳統(tǒng)書法藝術(shù)有了更深刻地認(rèn)識(shí)。聽了講座他覺得原來對書法的認(rèn)識(shí)過于淺薄。雖然自己愛好了幾十年的書法藝術(shù),但實(shí)際上并不真正了解書法的歷史及演變過程。喻得安曾經(jīng)出過一本水利方面的詩集,在現(xiàn)場他興奮地寫下一段話:樓蘭殘紙研究取突破,重琦先生作貢獻(xiàn)。
企業(yè)單位的美工付劉榮連連告訴記者,“真的很精彩,也很實(shí)用。這是我記錄的講座內(nèi)容。”他將記錄本展開讓記者過目。除了了解了樓蘭殘紙和增加了書法知識(shí)的積累,付劉榮還對楊重琦先生講座中講的一些生動(dòng)例子印象頗深。“如有人寫了幾十年的毛筆字,其實(shí)每天練習(xí)不過幾分鐘。乒乓球世界冠軍劉國梁一個(gè)動(dòng)作練習(xí)要十幾萬次,他自己練習(xí)書法用松緊帶綁手等等。”這讓人們明白練習(xí)書法是需要付出艱苦努力,走捷徑不下苦不可能寫出好書法的。這些話發(fā)人深省,他自己雖然一直從事美工工作,但確實(shí)如楊重琦先生說的那樣,一天練習(xí)毛筆字并沒有用上多長時(shí)間。
84歲的退休干部張國安講,這類講座一般都比較枯燥,但楊重琦講得既有知識(shí)性又有趣味性,講座自始至終一直吸引著聽眾。原來只知道楊重琦先生是一位資深媒體人,今天聽了講座還知道先生還是一名學(xué)者和書法家。
■相關(guān)鏈接
楊重琦:資深媒體人,書畫評論者。2002年創(chuàng)辦鑫報(bào),2008年創(chuàng)辦大西北網(wǎng)。現(xiàn)為甘肅省報(bào)業(yè)協(xié)會(huì)副會(huì)長,甘肅省新聞攝影學(xué)會(huì)副主席,大西北傳媒總裁,《鑫報(bào)》社社長,皋蘭書院院長,樓蘭書法研究機(jī)構(gòu)CEO,蘭州大學(xué)、蘭州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客座教授。著有《蘭州碑林賦》、《蘭州經(jīng)濟(jì)史》、《楊重琦書法作品集》、《百年中山橋》、《百年甘肅》、《隴上藏珍》、《中國書法初始化∶二至四世紀(jì)魏晉樓蘭殘紙研究》等著作。 (責(zé)任編輯:鑫報(b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