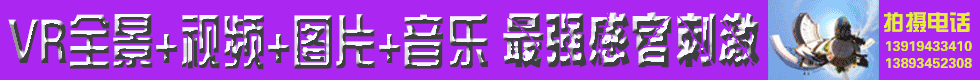書體在形成過程中,往往是與需求和書寫的材質、工具有關的。當隸書成為主流書體時,它的書寫速度太慢,不能適應社會的需求。另外,漢代紙的出現使書寫由少數人變成了多數人的交流工具,由于紙便于攜帶,書寫方便,出現了大量的書信和手札,這為行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魏晉時期行書尚未成為官方的書體,行書最初流行是在文人之間相互的信函和賣弄文字時所使用。樓蘭殘紙中多半是行書寫就,有的刻意,有的隨意,有工整,也有潦草,不過魏晉殘紙中有些公文是用行書寫的,這可能與樓蘭天高皇帝遠的地理特色有關。魏晉殘紙中的草書是中國書法瑰寶,它一方面是隸變行楷的書法原跡,另一方面則是中國書法、筆法、章法、墨法日趨完善的節點。可以說,魏晉殘紙中的行書囊括了今天所有的書法形式。更重要的是,許多筆法、章法在今天已經失傳,如果不是看到原件,不會想到字還能這樣寫。臨摹的樓蘭殘紙證明,當時的筆法很難被臨摹,幾乎不知怎樣寫成,這種豐富的筆法形態像萬花筒一樣展示了中國書法原生態的瑰麗。這些原生態書法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書法源泉,是王羲之之前的書法狀態,借助樓蘭殘紙和王羲之一樣在吸取原生態的書法資源。我們常說王羲之是達到了中國書法的頂峰,無人可及,從王羲之同時代的樓蘭殘紙中吸取營養將會開拓出新的書法世界,形成一個以臨寫樓蘭殘紙為主的樓蘭書派類。當今書壇就像是尋求突圍的一支部隊,陷入了苦悶之中,因為中國書法是一個具有強烈傳承色彩和個性張揚相結合的藝術門類。從進化中的角度講,任何事物都有量變到質變、由生到死的過程,書法也不例外。如果長時間地停止在一種書法資源的利用中,中國書法是沒有前景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樓蘭殘紙對中國書界無異于一顆原子彈,它帶來的沖擊波將會震撼書壇。因為樓蘭殘紙讓我們看到了真實的、初期的書法的姿態和語境,這是自唐代以來所沒有過的事情。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樓蘭殘紙是在自由的學風中發展起來的,它較好地解決了個人和流行的關系、正統和民間的關系。在表現個性和情感方面,更是質樸心理毫無造作,它讓我們看到了書與人、書與自然相互影響和融洽的關系。
據《中國書法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