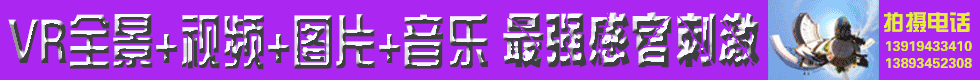彩繪銅飾木軺車

六博俑

王杖詔書令簡

絹底刺繡屯戍人物圖

葦胎針黹篋

龜形銅壺

黃釉陶盉

紡線錠 纏線板

木馬

墓穴洞口保留完整

“T”字型墓穴口

緊密排列的墓室清晰可見

殘存的墓室土墻

袁士鈾老人描述當年考古場景

鳩杖

磨咀子漢墓群全貌
武威磨咀子漢墓群:再現1800年前百姓的日常生活
大西北網4月11日訊 磨咀子漢墓群,在甘肅省武威市城西南15公里處的祁連山麓、雜木河兩岸。這里地勢起伏,形成丘陵地帶。西依西山頂,東接沃野,其間阡陌縱橫,有雜木河流過。這里很早以前就是便于人類居住、從事生產生活的好地方,因此,不僅有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而且有著極其豐富的漢代墓葬。同時,磨咀子也以出土大批漢簡、木雕、絲、麻、草編織物等重要珍貴歷史文物而聞名于世。
視線內一無所獲,難道皚皚白雪將一切秘密都再次封存起來?
四月,我們在武威采訪時,聽當地朋友說,在武威城郊一個叫磨咀子的地方,那里曾經有一處漢代的墓葬群,出土過大量精美的國寶級文物。磨咀子遺址早在2013年被確立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清明時節雨紛紛”,我們決定親自去祭拜一下,向那些在地下長眠的最早開辟河西走廊的老祖先們表達一下心中的敬意。
身處河西,人的思緒就會變得悠遠。
古時的河西走廊,地勢起伏,形成丘陵地帶,有祁連山豐沛的雪水灌溉養育,是西北內陸少有的一處水草豐美的寶地。
時間追溯從先秦至漢初,河西走廊上就分布有匈奴、月氏、烏孫等眾多游牧民族,一直到匈奴占據整個河西走廊。到了漢代,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春,漢武帝派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右擊匈奴,使整個河西走廊納入西漢版圖。隨后設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移民實邊,眾多的游牧民族和中原文化在這里相互交鋒、碰撞,最后水乳交融,煥發出新的生命。
一直到了唐代,河西走廊便成為了絲綢之路上最為重要的通道。
有著這樣豐富獨特的歷史,使得河西走廊上的重鎮武威擁有與眾不同的吸引力。
我們向長輩們探聽清楚磨咀子的路后,便在第二天一大早出發了。
從武威城出發,西南方向,直擊磨咀子漢墓群的所在地——新華鄉纏山村。一開始行程都很順利,沿著312國道行駛15公里左右,平坦的柏油路面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雪過后泥濘的山鄉土路。路邊的山巒,從山腳下開始,一路上全是白雪壓頂的冬麥苗,稀疏的村落,鄉間的小路曲曲折折,一直在纏繞著山體蜿蜒,難怪這里起名叫作纏山村。跟隨著山路的蜿蜒,我們也纏繞在了群山之間,停車問了好多老鄉,才慢慢找回到了正確的路,一條溪流在路邊時而出現,時而隱匿,最終,在溪流最為寬闊之處,老鄉告訴我們,我們到了,終于到達了目的地——磨咀子。
在蘭州早已是柳綠花紅,這里迎候我們的卻是茫茫的白雪。
問過老鄉才知,我們要找的磨咀子便在眼前這高高的土坡之后,停車徒步前行,爬上亂石土坡。
一爬上土坡,三塊漆黑的石碑便出現在了眼前,走近細看,碑上的文字就證實了我們所在的位置,這是磨咀子漢墓群的入口。
以文物部門立下的三座石碑為起點,沿著看似是路卻又不確定的路,一直朝里走著,目之所及,除去厚達10厘米的積雪和裸露在外的黃土,就只剩幾座巨大的土堆了。這里的漢墓群究竟在哪里?空無一人的四周,遠處是終年積雪的祁連山,墨綠色的松樹林,此刻已然是深黑色的。除去自己的呼吸,和身后留下的腳印,證明我們確實來過之外,視線內一無所獲,難道皚皚白雪將一切秘密都再次封存起來?
干燥少雨的氣候條件,使得埋藏地下的珍寶完整保存,哪怕是薄如蟬翼的絲帛和輕脆的漢代竹簡
我們找到了一位熟識且居住在磨咀子的袁士鈾老人,請他作為向導帶領我們去一探這白雪黃土之下的秘密。
老人家熱情地迎接我們,精神矍鑠,一點也看不出是已經七十古稀的老人,在一腳雪一腳泥的前行中,步伐矯健。
首先好奇急待袁老解答的就是此處的地名——磨咀子。為何此地會有這樣一個讓人無法琢磨的名字。袁士鈾哈哈大笑:“你們一路上來的時候,可曾注意到有泉水?”當然!我們回答說,就是跟隨著泉水一路問才找到磨咀子的。老人說,那就對了,這條泉水是紅崖溝的泉水,源頭就在這里。以前這里的泉水水勢很大,人們就在沿線修建了很多的水磨,基本上家家戶戶都有。順著水泉走一遭,看那水磨多得像是列著陣,蔚為壯觀,久而久之,這里就叫作磨咀子了。
一提起河西,現在的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黃土風沙,是干旱缺水,是人煙稀少,殊不知在這河西走廊的深處,還曾有過人們賴以生存的大規模的水磨。
可惜的是,這些可構成美麗風景的水磨現在基本上都被損毀或者拆除了,聽說只有下游的一戶人家還保留著唯一的一座。
除了這條紅崖溝的泉水,遠處還有源于祁連山脈東段冷龍嶺北側的大雪山,東北流于山谷,坡陡流急的雜木河,它是石羊河六大支流的第三大支流。
雜木河畔,水草豐美,便迎來了匈奴等諸多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才會有曾經的繁華富饒,而到后來中原的移民也來到這里,才會形成七十萬平方米左右的磨咀子漢墓群遺址。
磨咀子墓葬群分布在一片土山形成的丘陵臺地上,在南北長1000米、東西寬700米的范圍內,墓葬密布,非常集中。當我們走到之前看到的兩米多高的土堆旁時,老人說之前這里的地面就和這些土堆一樣高,一個連著一個的墓室就在這些土堆里面,曾經有段時間盜墓非常厲害,現在能看到的黑漆漆的墓穴口,有很多是當初盜墓賊留下來的。而我們身旁的這座土堆旁的腳下,就有一個一米多深的墓穴洞口,“T” 字形的洞口內是光滑的墻壁,可以看出當時這座漢墓內部的精細。
1955年、1959年,甘肅省博物館的專家們曾對磨咀子墓葬群有過先后兩次發掘,共清理漢墓37座,出土了一批珍貴文物。其中第6號墓出土了9篇《儀禮》竹木簡,首尾完整,次第可尋;第18號墓出土了王杖和“王杖十簡”,編為1冊,完整無缺。出土的這些竹、木簡及王杖均為建國以來考古工作中的重大發現,為研究漢代經學、版本學、校勘學、古文字學、簡冊制度、禮俗以及尊老、養老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轟動了史學界。
那么,為什么這些珍寶歷經1800多年后,仍然得以保存,能和今天的人們見面?
原來,這里的土質含堿性大,土質非常堅硬,加之是丘陵臺地,干燥少雨,即使是有大雨降臨,厚實的黃土也只會吸收一小部分,再加上這里的蒸發量終年大于降水量,雨水不會下滲,所以具有了保存地下文物的優越條件。因此,此處的墓葬及墓室內的隨葬器物保存較好,特別是一些不易存放的木器、絲、麻、草編物等都能夠保存下來。袁士鈾說,甚至有些三國魏晉時期的墓穴也有保留。
在這些出土的文物中,最為神秘的是一件造型獨特狀似腸胃的管狀“布袋”。這件布袋為紅褐色,“布袋”的兩端用一根繩子連接起來,“古代人用這樣的東西干什么呢?” 有人曾推測,這有可能是古代女性用來裝生活用品及飾物的東西,類似于現代婦女的背包,但是,這一推測隨后又有人反對,他們認為這樣的“裝扮”不合乎當時女性生活的習慣,況且對于墓室主人的性別目前仍不能做出定論。因此,“布袋”的用途成為一個至今未解的謎團。
經歷過上世紀五十年代兩次大的考古發掘,但考古界仍然對磨咀子漢墓充滿了希冀
在另一處大型的土堆前,袁士鈾站住了腳步。白色、黑色、黃色從上至下在土堆上分布:白色是雪,黑色是經過多年的風吹日曬,黃土硬化形成的硬殼,黃色便是厚實的土地。巨大的土堆一側,每間隔1米左右,就是一道殘存的土墻,布滿了整個土堆。這些土墻,就是曾經分隔一個個墓葬的墻壁。老人說,赫赫有名的《王杖十簡》就是在這里出土的。
磨咀子的墓葬一般為土洞墓,由墓道、墓門、墓室三部分組成。規模較大的墓葬還有后室、側室或耳室。墓道為斜坡式,墓門為過洞式連接溝通墓室。墓室多為長約4米、寬3米的長方形容穴,三人、雙人、單人葬均有,葬具為木棺。這些墓葬的主人,如今都已無法考證了,但從埋葬的方位看,那些分布較有規律,墓道頭頂上都鋪有形質、大小不一的方石的墓葬推斷,這些有可能為“家族墓葬”,其余的墓室因為此地土質堅硬,因而排布整齊,好似一間間房間,這些自然埋葬的是普通百姓。
在磨咀子墓葬群中,出土了很多珍貴的國寶級文物。代表著黃河流域最為典型的仰韶文化的陶器、造型優美的青銅器、栩栩如生的木雕、千年以前的農作物、精美完整的絲帛,以及完整成冊的漢代竹簡。
已經經歷過上世紀五十年代兩次大的考古發掘,出土了諸多精美文物,但考古界仍然對磨咀子漢墓充滿了希冀。
2003年,中日雙方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又對磨咀子漢墓及新石器遺址進行了新一輪的考古發掘,這次發掘歷經三年,將會有什么寶貝面世呢?
首次發掘,考古學家們就發現了兩座漢代壁畫墓,它是我國早期繪畫藝術的實物資料,也是研究漢代繪畫藝術的珍貴資料。磨咀子一號壁畫墓是單室土洞墓,墓室保存得比較完整,壁上畫有一幅墓主人出行狩獵圖。
磨咀子二號壁畫墓是一座規模較大的橫前堂、雙后室土洞墓,畫面分布在前堂后半部,頂端繪天體,有太陽、月亮、行云;后壁及兩側繪人物、鳥獸。人物有男有女,分別在做引體倒立、合掌靜坐、四肢曲伸、舉臂直立等導引行氣的健身運動。這是繼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帛畫導引圖出土之后的又一幅導引圖,也是我國最早的導引行氣壁畫之一。
在我國考古文物界,發現古代壁畫的為數不多。這些得以幸存的壁畫既向我們真實地展現了漢代繪畫藝術的成就,又使我們通過另一個側面了解了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了解了他們向往幸福、追求美好的內心世界和他們對世界的認識,對人生的感悟。武威的漢代歷史在這些壁畫中漸漸變得更加清晰起來。
更讓人欣喜的是,在磨咀子漢墓群的范圍里,2005年7月,考古人員又發現了一處距今約4000年的甘肅仰韶文化馬廠期新石器時代遺址。
這次遺址發掘是武威市歷史上較大的一次,共發掘甘肅仰韶文化馬廠期墓葬76座、灰坑43座、居住遺址8座、窯址6座,出土的器物有彩陶罐、陶球、紡輪、石斧、石棒、石刀、骨珠等,另外還有一件珍貴的彩陶壺。
這片遺址范圍較廣,面積達上萬平方米,考古人員對其中1000多平方米的遺址挖掘后發現,遺址內遺存物較多,層面內涵豐富。
出于對文物的保護,當年的探方都已經回填了,大地又恢復了它本來的寧靜。
想想要是在漢代,像古稀之年的袁士鈾也必定會有一把鳩杖吧!
在磨咀子漢墓群出土的文物中最為有價值且精美的就是于1959年秋在磨咀子第十八號墓出土的鳩杖和《王杖十簡》。
鳩杖,又稱鳩杖首。所謂“鳩杖”就是在手杖的扶手處做成一只斑鳩鳥的形狀。鳩杖在先秦時期是長者地位的象征,漢代更是以擁有皇帝所賜鳩杖為榮。
在漢代學者應劭的《風俗通義》中曾記載:據說漢高祖劉邦和項羽打仗,劉邦被打敗了,項羽緊追不舍,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劉邦躲藏在灌木叢中。當時正好有一只斑鳩鳥落在樹上,而且不斷地鳴叫。項羽的追兵趕到,理所當然地認為樹下無人,否則斑鳩鳥不會自由自在地鳴叫。由于有了斑鳩的掩護,劉邦終于脫了險。
傳說鳩為不噎之鳥,刻鳩紋于杖頭,可望老者食時防噎。《后漢書·禮儀志》:“玉仗,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所以,等到劉邦當了皇帝,為了紀念這只不同尋常的鳥,就做了鳩杖用來幫助行走不便的老人。此后,漢明帝還頒布了詔令:普天之下只要年滿70歲,無論貴族還是平民都有資格成為漢明帝的座上客,皇帝會贈送酒肉谷米和一柄做工精美的王杖。皇帝贈送的王杖也稱鳩杖,是賦予老年人特權的證明,受鳩杖的人相當于俸祿六百石糧食的官吏,要受到社會的尊敬,可以自由出入官府,可以在天子道上行走,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侮辱、打罵和虐待,有敢違抗者,以“大逆不道”罪公開斬首。可見漢代,高年以賜王杖,已經具備了尊老、養老、撫恤鰥寡孤獨廢疾之人的制度法規,由這些制度更可以看出當時尊老敬老的良好社會風氣。
跟隨鳩杖一起出土的還有“王杖十簡”。竹簡上的文字詳細記錄了當時關于“王杖”的內容,一共10枚,完整無缺,編為一冊。也解釋了一直以來困擾人們為何“七十賜王杖”“著鳩于杖末”的千年之謎。
“一勸世人孝為本,黃金難買父母恩。”在這片土地上傳唱的涼州賢孝,在出土的“王杖十簡”中切切實實的得到了印證。
從磨咀子漢墓群遺址出來,我們跟隨袁士鈾去了他家里。他家院子的圍墻是用一個個大小相似、圓滑的卵石堆砌而成,很具特色。我們疑惑,老人家的圍墻,山上的墓堆,都是用這種鵝卵石堆砌,那么在干旱的西北內陸,何來這么多的鵝卵石呢?老人指著屋前的泉水說道,剛才不是說過這里地名的來歷嘛,因為泉水水勢很大,有了水流,便帶來了鵝卵石,你們看到直到現在,河灘里依舊有那么多的石頭,人們甚至還用石頭來堆建房屋,就可想而知當年的水勢之大,也就更加印證了磨咀子的名字是名至實歸。
在袁老的家里,老人向我們講述了他和這片土地,他和磨咀子漢墓群的故事。在磨咀子出生、成長、成家,從呱呱墜地的嬰孩,到現在的七十古稀,老人的一輩子就是在磨咀子度過的。
曾經的絲綢古道,就在袁老的家門前經過。在袁老的童年時期,也同樣是走著15公里的絲綢古道,趕著驢車、騾車,把磨咀子的煤炭、糧食蔬菜,拉進涼州城,然后換得食醋和制衣用的布匹。直到312國道修建通車,這條古道才真正結束了它聯通西域,進入涼州城的使命。
雖然一直都是以普通百姓的身份生活在這里,但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幾次大型磨咀子考古發掘,老人也曾參與其中。直到1985年,正式成為了磨咀子漢墓群遺址的文物保護員,守護著這片祖先的痕跡,整整十年。十年間,每天夜里巡山,以防有盜墓賊前來,有時在巡山的時候,會發現一些銅錢、陶器、竹簡的殘片,都會保管好悉數上繳給國家,老人說,這些都是老祖先留下的東西,是不可多得的珍寶。
如今,留在這里的人們不多了,老一輩的很多都安睡在了山坡之上,年輕人都出去闖蕩謀生活了,袁老和老伴依舊守著這片土地。
想想要是在漢代,像古稀之年的袁士鈾也必定會有一把皇帝賜予的鳩杖吧!在磨咀子,在他的故鄉,頤養天年。
(本版文物均為磨咀子漢墓群出土 圖片為記者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