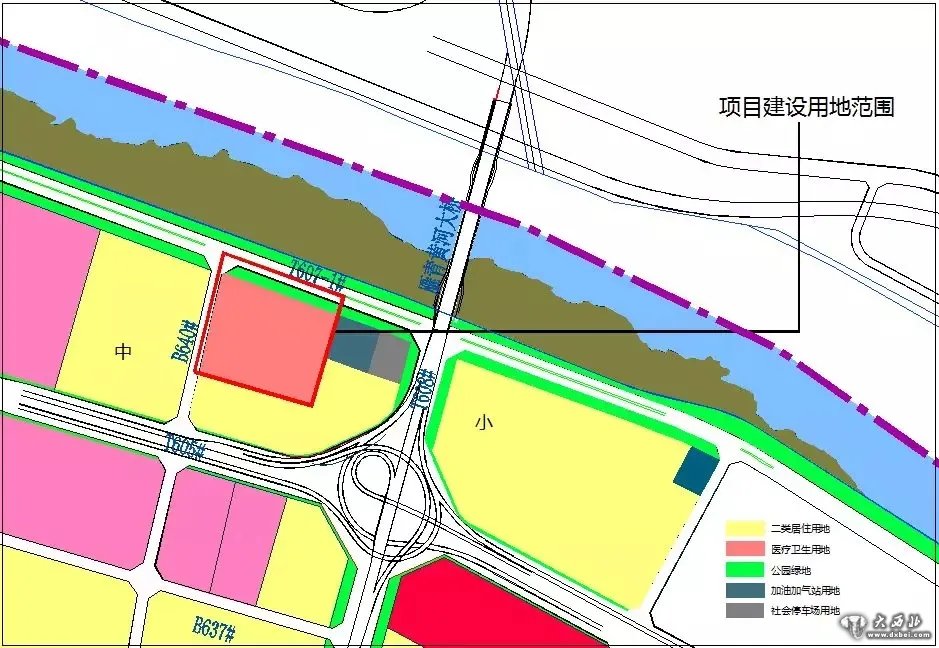湖南臨武,瓜農鄧正加的人生已然謝幕,盡管是以“突然倒地死亡”的姿態,那么突然地離開。死者長已矣,7月17日身亡,18日尸檢,19日便已下葬,因為“遲下葬一天賠付少10萬”(據央視網報道)。與此同時,臨武縣政府有關方面給予死者家屬的89.7萬元賠償,也在第一時間到位。涉案城管被刑拘,城管局長等人被免職接受調查。
幾天時間,一起引來舉國關注的公共事件,或將又面臨圍觀的退潮。但就在看起來地方政府追責(甚至是追刑責)的舉措正在進行時,另一方面的情勢卻是,收到賠償金的家屬開始選擇沉默,當地村民也“已收到指令,不準再多談”。兩相比照,又似乎并不那么合拍。瓜農鄧正加與城管爭執后“突然倒地死亡”事件,案情真相如何,值得也必須要進行繼續的追問。
按照目前的遺體檢驗情況,死者頭部、軀干、四肢等部位有軟組織擦挫傷,左前額部、左顳頂部、枕部頭皮下血腫,顱內有廣泛性蛛網膜下腔出血。而涉案城管被以故意傷害犯罪刑拘,也從一個側面表明,此前臨武官方所謂瓜農“突然倒地死亡”的說法并不客觀。央視采訪多位目擊者,“城管確實在打人”被得到證實,而且是多位城管“用拳頭和腳打”,但事發現場監控錄像至今沒有公布。
如果說對上述情況的處理,在社會各界的圍觀之下,臨武方面有基本的回應和處理,那么還有一些極其惡劣的細節,目前尚未有明確說法。比如搶尸體,臨武官方到現在依然強調這是“協助家屬轉移尸體”,卻并不解釋這一所謂經過雙方合意的協助行為,為何會動用數百名防暴警察?《新京報》等媒體援引現場人士說法,“警察先沖過來,手持警棍和盾牌,對現場圍觀者一頓暴打,傷者包括老人和小孩”,“砸碎冰棺搶走尸體,揮舞警棍追打家屬和圍觀群眾”,不少當日凌晨的現場圖片可以用“頭破血流”甚至是血腥來形容。在此之外,還有媒體記者在現場采訪時遭遇警察暴力對待,機器被砸、人被打傷,以死威脅。
這一場深夜搶尸戰、打記者風波,顯然不是“爭執”、“肢體沖突”可以解釋,如此多警力也不是城管就可以動用,曾到現場談判(后談崩)的臨武縣主要領導,是否應當為隨后因幾輪“搶尸”而引發的沖突升級承擔責任?往小里說,那些被打傷的群眾,其醫療救治費用誰來承擔,是否會被秋后算賬;往大里說,不當濫用警力,對群眾、媒體暴力相向的責任又該誰承擔?再進一步追問,那些讓死者家屬拿錢閉嘴,威脅村民“不準談”的力量,究竟是誰,究竟基于怎樣的邏輯,他們是否真的已經反省并認識到己方的錯誤所在?
如果說瓜農鄧正加的“突然倒地死亡”是此次事件的第一重危機,則之后的搶尸體、打記者事件,則是讓事件進一步升級的最主要誘因。而今,對事件的處理、問責僅僅圍繞“城管打瓜農致死”這一初始的情節展開,動用防暴警察讓新沖突上演、讓個案矛盾激化的相關責任,卻被低調冷處理,這顯然并非完整、有誠意的善后。
公共事件的當事人,在事件后期有怎樣的選擇,外界無權強迫,但如果是一種基于恐懼、被威脅而生的緘默,卻值得人們關注。“活著的人,以后還要繼續在那里生活”,類似說法的背景在于,作惡者并未真正被追究責任,依然對死者家屬、目擊者構成威脅。更嚴重的是,基于個案的討論始終無法進入制度反省的層面,被免職的官員“避風頭”之后還會復出,下令搶尸、打記者的官員甚至都不會有起碼的問責,這只會是殘缺、被勾兌過的真相與追責,且會令慘劇重復發生,矛盾積蓄并再次潛行于社會肌理中。就在日前,哈爾濱的大街上,又是城管打攤販打到頭破血流,記者采訪被圍毆。據說,涉事局長做了檢查。
瓜農鄧正加,曾癡迷賭博欠下外債,后浪子回頭,安分守己,成了勞模、農業科技示范戶。這個原本令人動容的勵志故事,因7月17日的那場沖突而中斷。事發當天,一般都是賣完瓜才去吃早餐的鄧正加,離開人世時可能還餓著肚子,人間慘象,莫過于此。除了幾個在一線動手的城管,還有誰該為此負責呢?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