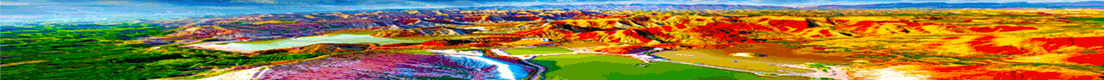自古以來(lái)書(shū)畫(huà)就有同源異流、用筆相通之說(shuō)。趙孟頫曰:“石如飛白木如籀,寫(xiě)竹還須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huì)此,須知書(shū)畫(huà)本來(lái)同”.鄭板橋亦有:“要知畫(huà)法通書(shū)法,蘭竹如月草隸然。”從張大千的藝術(shù)實(shí)踐和藝術(shù)成就看,是致力于繪畫(huà)的一生,也是致力于書(shū)法的一生。“
張大千說(shuō):”畫(huà)家自身便認(rèn)為是上帝,有創(chuàng)造萬(wàn)物的特殊本領(lǐng)。造化在我手里,不為萬(wàn)物所驅(qū)使,畫(huà)家可以在畫(huà)中創(chuàng)造另一天地,要如何去畫(huà),就如何去畫(huà),全憑自己思想。“
張大千豪放不羈、風(fēng)流倜儻的個(gè)性決定了他作品風(fēng)格強(qiáng)烈的抒情色彩,這不僅反映在繪畫(huà)上,而且反映在書(shū)法上。
張大千畫(huà)法的演變,實(shí)質(zhì)也是他書(shū)法的演變。每當(dāng)我們欣賞大千先生的書(shū)法作品時(shí),不時(shí)便會(huì)聯(lián)想起他的繪畫(huà)作品,其林茂幽深如《青城山圖》,宏大蒼茫如《長(zhǎng)江萬(wàn)里圖》,淋漓酣暢如寫(xiě)意荷花,寧?kù)o如工筆花鳥(niǎo)、簪花仕女,博大近《山高水長(zhǎng)》,飄渺如《巫峽清秋》,圓潤(rùn)如《耄耋圖》,清雋如《雙鴨圖》,郁勃如《紅梅》,富貴如《秋海棠》,險(xiǎn)峻似《廬山圖》等等,其意趣多樣,書(shū)畫(huà)意境統(tǒng)一,渾然天成。
然而,由于畫(huà)名所掩,大千先生獨(dú)具藝術(shù)風(fēng)格、拙厚古樸、挺秀清健的書(shū)法藝術(shù)卻往往被人忽視,以致冷落多年。
張大千一生留下的作品很多,一部分是純粹的書(shū)法作品,包括他書(shū)寫(xiě)的中堂、對(duì)聯(lián)、橫軸、扇而、書(shū)信、手卷等,一部分是題畫(huà)墨跡,由于其傳統(tǒng)功力深厚,他這一部分作品與其繪畫(huà)作品一樣,完整而有特色。即便從畫(huà)面中分離出來(lái),其獨(dú)立完整的章法,一氣呵成的氣勢(shì),也是頗令人驚嘆不已的。
從大千留下的作品看,他不僅書(shū)寫(xiě)行書(shū)、草書(shū),而且書(shū)寫(xiě)楷書(shū)、隸書(shū)、篆書(shū)。盡管楷隸篆作品極為少見(jiàn),但從現(xiàn)在能見(jiàn)到的作品中,我們不難看出其深厚的功力。其書(shū)如其人,豪放豁達(dá)、穩(wěn)捷、灰諧而富含靈氣,尤其隸、篆作品,拙樸古茂,中鋒行筆,渾厚勁挺、遲澀厚重,氣度軒昂。
張大千的用筆,有堰、有仰、有(奇欠),有側(cè),有斜,有停,有動(dòng)、有提、有按,或大或小,或長(zhǎng)或短,其沉著痛快,伸引隨勢(shì),順逆之變,皆暢其心機(jī),直通古人神采。古人評(píng)書(shū)有”變起伏于鋒抄,樞紐挫于豪芒“,這用來(lái)形容大千書(shū)法的用筆,是再恰當(dāng)不過(guò)的了。
張大千的用筆之所以如此精到和個(gè)性化,這是由于他在長(zhǎng)期的實(shí)踐中從不間斷對(duì)美的追求,并進(jìn)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用筆理論。
張大千說(shuō),”筆法的要點(diǎn),要平、要直、要重、要圓、要轉(zhuǎn)、要拙、要秀、要潤(rùn),違反這些要點(diǎn)那就是不妙。用筆要中鋒做主干,側(cè)鋒幫助它,中鋒把體勢(shì)建立起來(lái),側(cè)鋒幫助它,中鋒把體勢(shì)建立起來(lái),側(cè)鋒來(lái)增加它的意趣。中鋒要質(zhì)直,側(cè)鋒要姿媚。濕筆要重而秀,渴筆要取蒼潤(rùn),用筆要明潤(rùn)而厚重。不可灰暗而模糊。“
張大千還說(shuō),”要在剛勁快利中求柔美諧和,柔美諧和里要有剛勁快利,在柔美姿媚中找求剛強(qiáng)中正“,”下筆一定要有遒健、圓勁,生動(dòng)的意趣,一直連綿不斷,行筆要快而速,不可遲緩。“
張大千的書(shū)法融入了自己獨(dú)到的筆意,提按變化,順乎自然,一派陽(yáng)剛之美,給人以一種渾厚蒼茫的感覺(jué),作品自首至尾,筆觸扎實(shí),力透紙背,雄穆之勢(shì)撲面而來(lái)。這神寬博的基調(diào),與他晚年創(chuàng)作的潑墨潑彩山水畫(huà)作品,不能不說(shuō)是一種契合,也恰好是大千”藝術(shù)為感情之流露,為人格之體現(xiàn)“的最好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