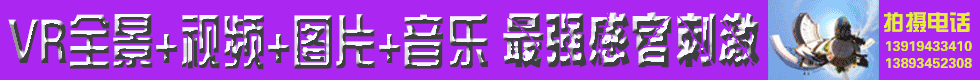大西北網白銀訊 會寧南部某鄉村。
山大溝深,是這里鄉村的標簽。遠遠看去,散落在山坳里的村落顯得有些蒼涼,在黃土地的底色映襯下,顯得格外空曠而寂寥。
沿著一條蜿蜒的土路而上,便是被疾控中心工作人員稱為“艾滋孤兒”的小嘉、小禾的家。除了他們倆,家里有年過七旬的爺爺,步入而立之年、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的爸爸李軍。世上尚有親人,卻被稱為“孤兒”,主要是因為姐弟倆被媽媽遺棄,因為得病,李軍又無力照顧孩子,加上村里人在得知李軍感染艾滋病后的對他們孤立抵觸,雖有親人在側,姐弟倆卻比孤兒還“孤”。
這個原本苦難的家,隨著7年前他們媽媽的離開更加寥落。媽媽離開的那一年,小男孩小禾年僅1歲,嗷嗷待哺。小女孩小嘉也只有4歲。對于他們而言,媽媽就是爸爸電話里偶爾傳出的陌生聲音,還有舊照片上模模糊糊的一個影子。
小嘉、小禾的媽媽走了幾年后,爸爸李軍也去外地打工了。從此,兩個孩子就跟著年邁的爺爺相依為命,幾畝薄田,就著咸菜饅頭,爺孫仨苦度日月。生活清苦,媽媽離家出走,爸爸遠走他鄉打工,和爺爺相依為命的平靜日子,卻充盈著姐弟倆最美的童年記憶。
幾年后,外出打工的爸爸突然回家了,卻老是生病,身體甚至不如老邁的爺爺,去年還去縣城的醫院住了一個月的院。沒有了打工的收入,還花掉了1萬多元錢的醫藥費,這個原本窘迫的家庭雪上加霜,日子越發難過了。
年幼的孩子們不知道爸爸得的是什么病,幾次追問,爸爸總說是肝炎。他們根本就沒想到,爸爸感染的是人人談之色變的“艾滋病”。
最為不幸的是,李軍感染上艾滋病的事情不知不覺中竟在村子里秘密流傳著。他們一家在村民的眼里漸漸成了異類,無論是大人還是孩子都遠遠地躲著他們。這讓年僅8歲,對世事還處于懵懂階段的小禾感到有些無助。“為什么以前的小伙伴們不和我一起玩了?”這是他常常問爺爺的話。
11歲的姐姐小嘉卻要成熟堅強很多,在她幼小的世界里,除了上學,每天最重要的就是騎自行車匆匆從離家10余里的學校趕回來給家里人做晚飯,風雨不改。做晚飯時,小嘉做菜和面,9歲的小禾則抱柴燒火。小禾在離家很近的教學點念書,教學點只設一到三年級,加上鄉村生源越來越少,2015年秋季已不再招生。這就意味著小禾在家門口已無學可上,只有和姐姐一樣去離家10余里的小學念書。
但是小嘉和小禾的爸爸李軍卻有更多的顧慮。村子里有關他的風言風語或多或少傳到了耳中,在這片他生活了40多年的故土上,街坊鄰居們都互相認識,誰家出了什么事,不用一天就能傳遍村頭巷尾,更何況是人人聞之色變的艾滋病。
在感染艾滋病之初,李軍感覺天塌下來了,躺了幾天,不吃不喝,滿腦子都是尋死的念頭。想到年邁的父親和年幼的兒女,他不忍心拋下親人就這么走了。他不再求死,但是感染上艾滋病后日子越來越難過。不能出去打工沒有了收入,加上不知怎么走漏消息后,雖沒有村民公開驅趕他,也沒有在表面上像躲瘟疫一樣對待他,但明里暗里他都會有一種被疏遠、被隔離、被孤立的感覺,在沉重的心理壓力下,李軍雖一直堅持治療,但心中郁郁難安。自感染后,他一直都是瞞著家人,如今村里有了關于他感染艾滋病的傳聞。稚子無辜,如果兩個孩子聽見后,不但會被村里人嫌棄,還會背負起很重的思想包袱。思來想去,他決定背井離鄉,帶著孩子們去縣城求學。
在一個陌生的環境里,將“真我”隱去。對于李軍而言,這無疑是無奈之舉。一個身染艾滋病的病人,兩個年幼的孩子,縣城里無親無故,甚至還沒有一份賴以養家的零工可干,進城求學的想法顯得瘋狂而大膽。百般無奈下,他想到了一位一直與他保持聯系并幫助他的縣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
每隔一段時間,李軍就會去縣疾控中心領取國家免費的艾滋病治療藥物。這是他與縣城唯一隔絕不斷的聯系。在這里,他可以把感染艾滋病后的心理重負找人宣泄出來,疾控中心工作人員的耐心開解,也成了他繼續走下去的精神慰藉。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他首先想到的,也是這些縣疾控中心里熟悉的陌生人。
了解到李軍的訴求后,縣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積極和教育部門聯系,為了確保李軍艾滋病感染者的信息不泄露,他們甚至還通過私人關系為孩子們入學四處找路子。最終,在縣疾控中心工作人員的幫助下,李軍找到了愿意接收兩個孩子的學校。
進城讀書讓小嘉和小禾很興奮,“我要去的學校是不是電視上那樣干凈漂亮的樓房,玻璃亮晶晶的,操場是彩色的?”小禾總是這樣念叨著。安靜懂事的小嘉,也在為進城做著力所能及的準備,她早早就拆洗好了被褥,收拾好了書包,悄悄為她和弟弟生命中的第一次遠行準備著行囊。
如今,李軍帶著兩個孩子在縣城里找到了安身之處,孩子們也如愿走進了理想中的漂亮學校。而橫亙在這個苦難家庭面前的,還有很多的沉重的現實問題。如何在城里養活孩子、供他們念書?習慣了鄉野的孩子們能否適應城市的節奏?那遙不可及的未來,出路到底在何方?這些問題的答案,李軍依然在苦苦求索。
記者手記:
稚子無辜 勿讓歧視再度創傷幼小心靈
按照艾滋病專業術語,受艾滋病影響兒童是指艾滋病致孤兒童、父母一方感染艾滋病或因艾滋病死亡的兒童、攜帶艾滋病病毒或感染艾滋病的兒童。小嘉、小禾就屬其中。
上學難不僅是小嘉、小禾的難題,而是幾乎所有受艾滋病影響兒童的難言之痛。記者查閱公開資料顯示,我國目前報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約50萬。由于父母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經由母嬰傳播,一出生就受到感染的兒童也并非少數。不幸中的萬幸,小嘉、小禾沒有感染艾滋病,但他們的生活卻時時籠罩在艾滋病的陰影下。
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能否享受法律賦予的受教育權成為一個不得不正視的問題。針對這些孩子在入學、就醫等方面遇到的種種困難,我國相關部門已出臺過諸多幫扶政策。2004年,我國政府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實施“四免一關懷”政策,其中包括“對艾滋病患者遺孤實行免費就學”。2006年,國務院頒布了《艾滋病防治條例》,其中明確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享有的婚姻、就業、就醫、入學等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
國家衛生計生、教育、民政、財政等多部門曾先后印發多文件,其中均對受艾滋病影響兒童就學、就醫、生活救助等方面作出了明確規定:“加強權益保護,保證受艾滋病影響兒童接受學校教育。”
2014年年底,國家衛生計生委等三部門聯合發布了通知,要求“進一步落實受艾滋病影響兒童接受教育的合法權益”,要求“各地依法加強對受艾滋病影響兒童的隱私保護”,泄露艾滋病感染兒童信息將嚴處。但通知中卻沒有明確要求普通學校不得拒收受艾滋病影響兒童,只是規定“對少數入學困難的受艾滋病影響兒童,各地教育部門要妥善安排”。
雖然受艾滋病影響兒童享有平等入學權利的規定早已寫入相關文件,但由于公眾對艾滋病缺乏足夠了解,“談艾色變”的現象仍然存在,受艾滋病影響兒童不得不面對入學難問題。
消除對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和受艾滋病影響兒童的社會歧視是一道任重而道遠的考題。陰霾的背后,也有那么多的溫暖和關愛存在。在201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習近平主席強調:“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關系人民生命健康、關系社會和諧穩定,是黨和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這足以證明了該項工作的緊迫性。然而,防治艾滋病是個綜合性極強的工程,需要全社會各個層面的通力合作,如果光靠醫療機構的專業防治,顯然是遠遠不夠的。那才是最根本的一步。特別是,消除社會歧視,是防治艾滋病的關鍵一步。
面對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影響兒童,當每一個“小我”不再吝嗇愛和微笑,伸出雙手接納他們,讓他們感受到掌心的溫度和愛的甘露,這份寬容就會像一團星星之火,通過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對所有籠罩在艾滋病陰影下人們的關愛定將形成燎原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