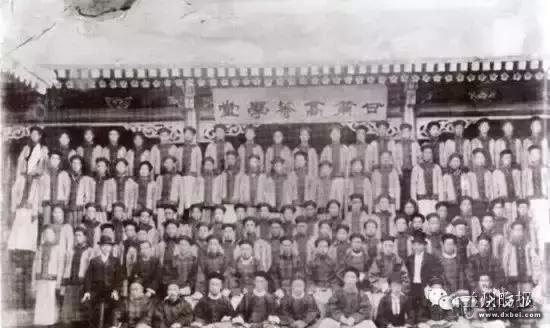
甘肅文高等學堂(又稱甘肅高等學堂)創辦于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是在歐風美雨沖擊下,培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人才的學堂,在劉光蕡、劉爾炘等名師的辛勤教育下,那些昔日研習八股文、試帖詩,一心想金榜題名的士子,盡情吸納新知,視野突然開闊,愛國思想倍增,他們畢業后成為甘肅除舊布新的重要社會力量。
奉“新政”開辦甘肅文高等學堂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慈禧太后攜光緒帝逃往西安,痛定思痛,慈禧太后于次年,以光緒帝名義頒發“預約變法”上諭,揭開清末“新政”序幕,陸續出臺停科舉、廢書院、興學堂等改革方案,使中國傳統社會在近代道路上邁進。
地處邊陲的甘肅也不例外,陜甘總督崧蕃設立甘肅省大學堂、甘肅省武備學堂,繼任總督升允設立甘肅省速成師范學堂、蘭州府中學堂、求古學堂、甘肅省優級學堂、甘肅省農林學堂、甘肅省礦物學堂、甘肅法政學堂,尚有電報學堂、皋蘭縣高等小學堂、蘭州織呢藝徒學堂、蘭州仵作學堂、甘肅省高等巡警學堂等,皆在蘭州城區。這些雨后春筍般的新式學堂,給一千多年的古城帶來新氣象,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甘肅文高等學堂。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清廷詔令各省創辦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創辦中學堂,各縣創辦小學堂。陜甘總督崧蕃任命候補知府楊增新為提調,創辦甘肅大學堂,并令楊增新先赴北京、天津及東南各省考察創辦大學堂的情況,將大學堂校園的建筑、教學、管理等情況,一一筆記,返回后仿照辦理。順便在北京聘請俄文、法文、日本文教習。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清廷又詔令各省緩辦大學堂,將各省籌辦大學堂的款項提交朝廷,以合力創辦京師大學堂,因此,甘肅大學堂改為甘肅文高等學堂。文高等學堂的學制,介于大學堂與中學堂之間,約略等同于民國初期的專門學校。
楊增新等人一邊建校,一邊招生開學。崧蕃聘請陜西咸陽劉光蕡為總教習,劉與陜西籍教習住在蘭山書院,先招收的20多名學生,則在甘肅舉院外供給所及官庭兩個小院上學、住宿。
劉光蕡(1843年-1903年),字煥唐,號古愚,陜西咸陽人。舉人,會試不中,便以張載所言“孰能少留意于科舉,相從于堯舜之間”自勵,絕意仕途,倡導廢八股,習算術,立新學,舉實業,培養新型人才,與康梁變法運動相呼應,稱“南康北劉”,任味經書院、崇實書院山長,講求實學,培養實用人才。戊戌變法失敗后,陜西巡撫解聘劉光蕡的崇實書院山長,劉退居禮泉縣九山下的煙霞草堂繼續講學。著有《立政臆解》《學記臆解》《大學古義》《孝經本義》《論語時習語》《煙霞草堂文集》等。
劉光蕡是維新派北方的領軍人物,四川大學堂、甘肅大學堂相繼禮聘總教習,他婉拒了各方面條件優越的四川的聘書,卻接受了甘肅的聘書。其中的緣由是,甘肅“居陜西上游,俄人雖得旅順,不能逞志于黃海,必將轉而逞志西北,蓋海戰俄不如英也,陜甘之患近在眉睫。”沙俄虎視眈眈,覬覦西北,先是新疆,接下來就是陜甘。面對如此危局,劉光蕡選擇了甘肅的聘書,目的就是為甘肅培養有個性、有才能、愛國報國的人才,協同陜西士人,共御外侮。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陜甘總督崧蕃派禮泉縣唐知縣給劉光蕡送去甘肅大學堂總教習聘書及路費,劉欣然接受,并復信崧蕃,陳述辦學理念:“時事艱危,需材亟孔,朝廷整頓學術,別頒教規。挑入學堂肄業,必皆少年。成材須在十年,而凡耆宿、碩儒,又各揶揄于后,則后生小子皆狐疑,心無定見,學必多歧,恐十年仍不得可用之材,則辜負設學之苦心矣。竊擬大學堂先設一延賓館,一面挑選肄業之士,一面博采全省齒德隆重、名望夙著者三四十人,集聚其中,講論教育之法。制軍為主,數日一臨,蕡為支賓,時參末議。不過三月,此三四十人,必皆曉然于朝廷改變學校之用意所在,俾歸其鄉,倡辦中、小及蒙學堂,既去阻力,兼獲多助,所費無多,不期年而樂育之懷,可曉然于全省矣!”
廢書院,興學堂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卻為多數人不理解,尤其是各府州縣的耆宿、碩儒,尤為不理解,時而嘲笑,進而阻撓,致使青少年狐疑不止,興學堂之事遇到巨大阻力。為此劉光蕡建議在甘肅大學堂臨時先設延賓館,選代表人物三四十人,其中有學生,也有全省各地的德高望重的紳士,集中館內,討論興學堂的問題。提議陜甘總督崧蕃為主人,劉光蕡本人接待來賓,并參與討論。這樣研討不足三個月,來賓皆能了解朝廷改變教育制度的用意,獲得興學堂的共識,他們回到地方,必能協助地方官興辦蒙學堂、小學堂、中學堂。延賓館究竟設立與否,史料并無記載。然而自此以后,全省各級各類學堂得以順利興辦,則是不爭的事實,這與陜甘總督崧蕃等高官聽取劉光蕡的建議不無關系。
甘肅文高等學堂校址選在一處舊軍營,位于蘭州小稍門外暢家巷的為前路后營舊址。早在光緒五年(1879年),陜甘總督左宗棠就利用這些舊軍營,建為蘭州織呢局,自東向西排列,分為東、中、西3廠,后因經營不善,織呢局不景氣,時停時復。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秋,將東廠建為甘肅文高等學堂,次年將西廠建為甘肅武備學堂,中廠為慘淡經營的蘭州織呢局。甘肅文高等學堂校舍內建圖書樓1座,齋舍3院、教室6座、理化教室1座。學生分別住在齋舍的東、南、北三院里,后來學生增多,一部分住到武備學堂的一所單院中。
新校舍建成,學生遷入,在這里上學。學堂設提調1員,總辦(后改為監督)1員,副辦1員,總教習1員,教習若干員,監堂、文案、庶務、會計、管書各1員。另雇聽事1員,掌管上下課打梆子,轉送師生間的文件;齋夫3員,每齋1員,打掃學生宿舍,提送開水,代學生外出購買零用物件。學堂經費每月支銀5000多兩。
甘肅文高等學堂的學生有100多人,來源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以生員資格報考的,有廩生、增生、附生等;第二部分是癸卯(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科鄉試薦卷而未取為舉人者;第三部分是由各縣保送的生員;第四部分是癸卯科舉人。從學生的籍貫說,主要是甘肅省(今甘肅、寧夏、青海三省區)的,新疆省只有4名。從年齡來說,最大的天水人郭士林、新疆人解林,都超過40歲。年齡最小的有隴西人王天柱、秦安人王守模,只有十六七歲。多數學生在二三十歲之間。
維新變法領袖擔綱首任總教習
甘肅文高等學堂的課程設有經學、歷代學案、史學(中國歷史、外國歷史)、地理(中國地理、外國地理)、外文(分為英文、法文、俄文、日文)、理化、教育心理、數學(分為算術、代數、幾何、三角)、博物、體操、法制、兵學、機械、圖畫、萬國公法、修身等。學生用六年時間,學完這些龐雜的課程,外文要專修一門,兼修一門。
經學先由總教習劉光蕡講授,后由總教習劉爾炘講授經學、修身,并根據《梅氏叢書》《數理精蘊》為依據,不定期講授數學。中國歷史由蘭州進士孫尚仁、鎮原舉人慕壽祺分別講授。外國歷史由蘭州舉人史廷琥講授。地理由副辦、同盟會員、長沙人易抱一講授。法文由雙弗講授。俄文、日文由山西祁縣舉人、北京同文館畢業的閻澍恩講授。英文由鐘世瑞講授。萬國公法由副辦張某講授。日本教習梅村次修講授博物,高橋吉造講授理化,崗島誘講授教育心理學。梅村次修、崗島誘認識漢字,不會說漢語,講課時又無翻譯人員,就在黑板上板書漢字講義。崗島誘則用日語講一段講義,然后翻譯成漢語,板書在黑板上書法整齊,文理通順,學生們評價很高。而高橋吉造講課時,由日本留學生范恒同步翻譯。法文、俄文難度大,只有一二十個年紀輕的選修。大多數學生,年齡偏大,就選修英文、日文。外文、數學課,上課不分班,其他課程則分班上課。
光緒二十九年(1903)正月十五后,劉光蕡攜夫人和二子,以及學生魏之杰、王章一行風塵仆仆西行,二月二十后抵達蘭州,受到崧蕃等官員的盛情接待。劉光蕡立即為甘肅文高等學堂制定章程規則,首先制定《功課提要》:“學堂課程,每日時刻,華文僅三點鐘,非輕華文也。以諸君身列庠序,皆讀書習文,此時華文不過溫習,而西文則全未寓目,時勢又迫,不能不略重西文也。溫習華文,當專重經史。”從課程的時間安排上,側重西文,即外文與西方的科學知識,而華文即經史,只安排三個小時,體現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中學”是指以孔孟之道為核心的儒家學說,“西學”是指近代西方的先進科技,“西學”為“中體”服務。這是湖廣總督張之洞為了調和統治階級頑固派和改良派之間的矛盾,總結洋務實踐的口號。
“專重經史”分為溫經與閱史兩部分。溫經有四項:即倫理、政治、文辭、習字,都要閱讀《書經》,每天不超過五千字,筆記疑問及心得。倫理既要學習中國傳統的“五倫”,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的道德關系,又要學習新倫理“四對”,即對己身、對家族、人群、國家。何以研習新舊倫理道德呢?劉光蕡說:“吾中國有倫理而無政治,尊君以文而不以心,君民之間,情不結以同胞宗子,義不聯以師友主賓,群無首而渙散乖離,人方以我無倫理而野蠻我、禽獸我,而敢望與人友?故吾輩今日讀書,當注意倫理以修政治始。蓋必吾有君而后,人心群于一,以修政治,人自不敢侮我、詈我,而引以為友矣。故倫理為主政之源,政治即修倫理之道。”文辭與字則是表達倫理與政治的工具,因此兩者不可廢棄。習字要以快為主,曾文正公曾說:“人須日書二萬字,方能足用。”這是他在行軍作戰中的閱歷,值得學生仿效。習字時必須講求形聲,形的認知,需要研習《說文解字》,聲的學習則要研究音韻學。
閱史分為歷史事實和典章制度兩項,都要閱讀《通鑒輯覽》,每天讀五頁,筆記疑問和心得。劉光蕡為學生開出的書目有《東華錄》《滿漢名臣傳》《圣武記》,以了解本朝的興衰治亂;《十朝圣訓》《皇朝三通》《經世文編》,以了解本朝的法制。他認為,讀各朝史,要思考、分析該朝的風俗、人才、國勢,研究這三點,該朝的興衰可以預定。典章制度涵蓋面廣,除天文、歷算歸入算學外,地域、官制、財賦、兵刑、農田、水利、物產、學校、選舉、邊防、外交等,均須留心,并與現實情事相比較,方能有益。同時還要閱讀報章雜志,研讀各國歷史及其典章制度之書,獲益將百倍于舊史。
劉光蕡在《功課提要》最后,勉勵學生:“以上各類,諸君自諒精力,能兼若干門,則專精于此數門,他則涉獵而已。”對于讀《四書五經》、寫八股文、試帖詩、策論的甘肅士子來說,《功課提要》打通古今中外,以經世致用為要務,不啻黑暗的閃電驚雷,使他們眼界大開,知道了學新知、救國家的途徑。
文高等學堂沿襲書院膏火銀制度,本科學生每月可領津貼二兩四錢銀子。每月由陜甘總督、甘肅布政使、甘肅按察使輪流出題月考,成績優秀的,可得獎金一二兩或幾百文麻錢。還有“貼堂”制度,選取學生的好文章,貼在講堂上,供學生欣賞。有個叫侯垣的天水學生文章做得好,經常貼堂。教習還將學生關于經學的心得、見解,見解新穎的史論,批改后令學生謄清,再送教習,積攢到相當篇幅,排印為《經學日記》《史學日記》,分贈或銷往全省各府州縣,供各級學堂的師生觀摩。
由于班級越來越多,師資缺口越來越大,文高等學堂遂實行“領班”制度,也就是選拔學習成績優秀的高年級學生,為低年級學生上課。如領班趙元貞、王兆麟、張家骙講授數學,趙學普講授博物。這些領班每月可得八兩銀子的代課費。
文高等學堂為所有學生提供數學、外文教科書、圖畫紙以及鋼筆、墨水。其他經學、史學等書籍,均由學生購置。學生穿校服,一律著短裝,衣襟及下擺為深色貼邊,冬天戴暖帽,夏天戴涼帽,均置銅頂,并剪去辮子。不準吸煙、喝酒。睡熱炕,點黑瓷清油燈照明。學生一般自由組團,雇廚師做飯,有的學生為省錢自己做飯。
甘肅文高等學堂除本科外,另設有師范館和預科。師范館招收學生數十人,絕大多數為舉人、貢生,還有一名進士,他就是靜寧人孫云錦。這些學生年齡偏大,一般三十多歲,甚至有四十多歲的,只有蘭州舉人王鑫潤二十六七歲,算是最年輕的學生。貢舉進士何以紆尊降貴上師范館呢?這是因為科舉考試廢除,他們失去了進一步考取功名、進入仕途的門徑,謀生發生了危機,此其一。其二,師范館學制為一年,畢業后即可派往各府州縣開辦小學堂,即可擁有一份體面的工作,薪水頗為可觀。其三,師范館學生每月還發津貼八兩銀子,待遇優厚。預科不拘資格,自由報考。
劉光蕡任總教習一個月,就使大學堂走向正規,學風丕變。他每天講授經學兩小時,批閱課卷,還要檢查算學課卷。課后召優秀學生交談,答疑解難。入夏,他的咯血病復發,仍然講課批卷不停,師生勸他休息,不聽。而各方來請益者絡繹不絕,他抱病解答或回信。七月初一,憂患時疫,熬至八月十三,終至不起,時年六十一歲。十月,歸葬咸陽故里。劉光蕡雖然只當了短短的七個月總教習,但對甘肅文高等學堂設立、運行具有開拓性的意義,用維新思想對于學生的啟迪具有啟蒙意義。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甘肅文高等學堂的二十八名學生,出資鐫刻《劉古愚先生德教(教思碑)碑》,樹立在東稍門外舊大路東口,1980年以前猶在。
劉光蕡的繼任者是劉爾炘(1864年-1931年),字又寬,號曉嵐,又號果齋,晚號五泉山人,蘭州鹽場堡人。光緒己丑(十五年,公元1889年)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不謁見權貴,見朝廷腐敗,事不可為,遂辭官歸里不復出。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秋,陜甘總督崧蕃禮聘劉爾炘為總教習,一直到文高等學堂結束。講授經學,先后講授《尚書》《周易》《詩經》《春秋》。
精英門生的報國情懷
自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文高等學堂創辦以來,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三十四年分兩批,共有100多名學生畢業,正科即告結束。預科及宣統元年(1909年)所招一班附中,到宣統三年(1911年)畢業,文高等學堂宣告結束。1913年,在原址建成甘肅全省中學堂,幾經演變發展,成為今日的蘭州一中。
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響應,而陜甘總督長庚卻集中財力,派甘軍攻打陜西民軍,擬奉迎宣統帝偏安西北,省城蘭州人心惶惶,當局無暇亦無財力支撐文高等學堂,一代名校從此結束。
但是,文高等學堂的學生卻在20世紀上半葉發揮著很大的作用。這還要從甘肅文高等學堂懸掛著的劉爾炘撰書的那副楹聯說起:“我都是黃帝子孫,俯仰乾坤,何堪回首;你看那白種族類,縱橫宇宙,能不警心。”來自全省各州縣的士子朝夕寓目,相互激勵,刻苦學習,飽覽中外書籍,縱觀五洲風云,民族意識與愛國熱情高漲,畢業生成為甘寧青新政界、教育界的中堅力量。
首先是讀經不乏民主思想。武昌起義后,全國各省接連反正,清廷被迫致電各省征詢國體意見,陜甘總督長庚頑固堅持帝制,具有民主與民族思想的文高等學堂教習慕壽祺、畢業生鄧宗、水梓等與省城官紳王之佐等,皆為同盟會員,他們力主共和政體,并力主撤回攻陜甘軍,為最后促成甘肅共和做出了努力。
其次是學成之后不忘反哺桑梓。文高等學堂畢業生有的回到各縣,興辦學校。有的赴北京深造,個別人留學美國、日本,畢業后,他們返回甘肅獻身教育等事業。例如鄧宗(京師大學堂畢業)創辦了甘肅省立女子師范學校(今蘭州三中)、牛載坤(京師測繪學堂畢業)創辦了省立工藝學校(蘭州理工大學的前身)、趙元貞(京師大學堂畢業,赴美國留學,獲冶金學博士)創辦了志果中學(今蘭州二中)。趙元貞任實業廳長、水梓(京師法政學堂畢業)任教育廳長,推動了經濟與教育事業的發展。
甘肅文高等學堂是中國傳統書院與近現代學校之間的一種過渡形式,它為近現代學校甘肅學校的興辦積累了經驗,尤其是對中國傳統文化與歐美文化如何融合做了可貴的探索,它的畢業生服務桑梓,在各個領域都做出不俗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