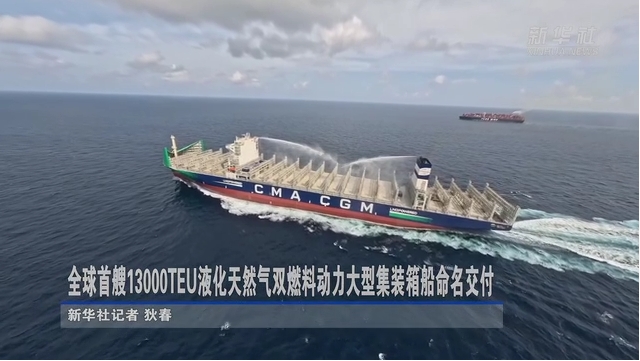如果說中華文明史是一部絢爛長卷,那么河西走廊連接?xùn)|西、融通中外的篇章就是其中的彩頁。
絲綢之路、玉石之路、茶馬古道,見證了不同歷史時(shí)期賦予河西走廊的偉大使命。自漢以降,從史無前例的鑿空到全方位的經(jīng)略,從彼此往來到深度融合,一代又一代的使者、行旅跨越千山萬水,在聲聲駝鈴中跋涉前行,讓河西走廊薈萃了無數(shù)史詩和動(dòng)人故事。

2024年1月22日在河西走廊中段。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張睿 攝
“三邊鎖鑰河山壯,萬國車書驛路通。”這條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內(nèi)蒙古高原交會(huì)地帶的狹長廊道,猶如“國之長橋”般承載起啟東承西的重任,為推進(jìn)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和人類文明進(jìn)步注入強(qiáng)大動(dòng)力,闡釋著中華民族兼收并蓄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和合作共贏的偉大襟懷。
昔日響徹河西走廊的駝鈴聲已塵封進(jìn)歷史。而今,這里成為促進(jìn)東西文明對話、加強(qiáng)中外交流的獨(dú)特舞臺。敦煌文博會(huì)搭建起交流互鑒的新平臺,治沙抗旱的“中國方案”從這里走向世界,見證新西蘭和中國友誼的培黎學(xué)校在這里續(xù)寫傳奇……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xù)推進(jìn),河西走廊“一橋飛架貫東西”的使命已經(jīng)奏響新時(shí)代強(qiáng)音。
大陸橋:連通世界的交通要道
2023年11月21日,伴隨汽笛長鳴,“敦煌號”國際貨運(yùn)班列從敦煌火車站出發(fā),一路向東,直奔海洋。列車上裝載的1000噸產(chǎn)自敦煌的石棉,先運(yùn)抵天津港,最終以鐵海聯(lián)運(yùn)的方式抵達(dá)泰國曼谷。
茫茫戈壁,大道縱橫。像百川匯海那樣,“敦煌號”列車出發(fā)后不久,就從一條鐵路支線駛上西北交通主動(dòng)脈——蘭新鐵路。沿途,筆直的鐵路、寬闊的高速公路、銀光閃閃的特高壓輸電線路,以及油氣管廊,與蘭新線平行而建,沿河西走廊向東、向西蜿蜒。立體交互的基礎(chǔ)設(shè)施網(wǎng)絡(luò)將廣袤的大西北與環(huán)渤海、長三角、珠三角等經(jīng)濟(jì)圈相連。

2023年11月21日,“敦煌號”(敦煌-天津-泰國)鐵海聯(lián)運(yùn)國際貨運(yùn)班列首發(fā)。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張曉亮 攝
東起江蘇連云港,西至荷蘭鹿特丹,新亞歐大陸橋是“一帶一路”“六廊六路多國多港”架構(gòu)的組成部分。其中,從連云港到阿拉山口,河西走廊是必經(jīng)之地,也是關(guān)乎新亞歐大陸橋暢通的“鎖鑰”。
打開中國地形圖,河西走廊的南部,是高寒缺氧的巍巍青藏高原;向北,是由烏蘭布和沙漠、騰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組成的千里大漠。古時(shí),只有沿河西走廊這個(gè)水草豐茂的天然廊道東來西往,才最經(jīng)濟(jì)、最安全。于是,人們在這里建起長城、官道、驛站等“基礎(chǔ)設(shè)施”,全力保障河西走廊的暢通,為過往使者、商旅提供補(bǔ)給,搭建起聯(lián)通中原與西域的陸路通道。整個(gè)河西走廊,仿佛一座以綠洲為“橋墩”,各類道路、管廊為橋體的“大陸橋”。
河西走廊的暢通與否,一直關(guān)乎國家戰(zhàn)略:左宗棠經(jīng)由河西走廊進(jìn)軍新疆收復(fù)領(lǐng)土;抗日戰(zhàn)爭時(shí)期,蘇聯(lián)大量援華物資經(jīng)由河西走廊源源不斷運(yùn)往內(nèi)地;新中國成立以來,河西走廊的基礎(chǔ)設(shè)施聯(lián)通迎來空前大發(fā)展。
1952年,蘭新鐵路破土動(dòng)工,三萬勞動(dòng)大軍鏖戰(zhàn)烏鞘嶺;1962年,蘭新鐵路全線竣工,河西走廊結(jié)束了沒有鐵路的歷史;1990年,新亞歐大陸橋貫穿河西走廊;20世紀(jì)90年代末,從連云港到霍爾果斯的連霍高速開始建設(shè)……
進(jìn)入新時(shí)代,乘著共建“一帶一路”的東風(fēng),一個(gè)更加立體、通暢的黃金通道在河西走廊加速建成。
2012年,甘肅敦煌至格爾木鐵路開工建設(shè);2014年,蘭州至新疆高速鐵路全線通車;2015年,酒泉—湖南±800千伏特高壓直流輸電工程開工建設(shè);2019年,蘭州至張掖三四線鐵路正式進(jìn)入建設(shè)階段……
在蘭張三四線鐵路武威東站站房的施工現(xiàn)場,工人們正有條不紊地搬運(yùn)板材、安裝設(shè)備,機(jī)器轟鳴聲、焊接聲此起彼伏……
中建鐵投集團(tuán)施工標(biāo)段項(xiàng)目經(jīng)理左君說,這條鐵路建成通車后,河西走廊東端節(jié)點(diǎn)城市武威至蘭州的旅行時(shí)間將由原來的4小時(shí)縮短一半以上,推動(dòng)河西走廊更好融入全國路網(wǎng)。
時(shí)空變幻,歲月如歌。如今,河西走廊這座“大陸橋”,在時(shí)間洗禮下,沉淀為一條更寬廣的臂膀,連接?xùn)|西,貫通南北,書寫著中國式現(xiàn)代化嶄新篇章。

2023年5月26日拍攝的中鐵一局蘭張三四線鐵路下河?xùn)|特大橋鋪軌作業(yè)現(xiàn)場。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陳斌 攝
共贏橋:雙向奔赴的經(jīng)貿(mào)商道
漫步敦煌,如入漢唐。這座城市,早在兩千年前就見證過東西往來的繁榮。如今,它依舊盛大輝煌,吸引著萬千游客。
世界文化遺產(chǎn)敦煌莫高窟里,當(dāng)看到壁畫上高鼻梁、深眼窩的西方商人,牽著載滿貨物的駱駝,與東方的商隊(duì)相遇時(shí),游客們不禁驚嘆:古與今,一步之遙。
“商旅往來,無有停絕。”西漢時(shí)期東西方商貿(mào)往來的景象依然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不斷上演:從農(nóng)產(chǎn)品到新能源裝備,經(jīng)貿(mào)往來、技術(shù)交流日益頻繁。
在敦煌市轉(zhuǎn)渠口鎮(zhèn)的甘肅本源興農(nóng)產(chǎn)品有限責(zé)任公司,工人們忙著精選、包裝貯藏在恒溫保鮮庫的紅提葡萄。海關(guān)工作人員現(xiàn)場辦公,把關(guān)果品包裝、運(yùn)輸全流程,確保“搶鮮”出口。

2024年1月22日,在位于甘肅省敦煌市的甘肅本源興農(nóng)產(chǎn)品有限責(zé)任公司,工人在包裝紅提葡萄。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馬希平 攝
兩千多年前,葡萄與胡蘿卜、胡麻、大蒜等作物,通過河西走廊東傳進(jìn)入中原地區(qū)。兩千多年后,產(chǎn)自敦煌的3000噸優(yōu)質(zhì)紅提葡萄由此出海,銷往泰國、孟加拉國、馬來西亞、白俄羅斯等國家。
令人稱奇的是,河西走廊這片戈壁灘上不僅種出了瓜果蔬菜,還種出了“太陽”。
在敦煌市區(qū),許多游客能看到20公里外戈壁灘上的耀眼光點(diǎn)。那些光來自1.2萬面“超級鏡子”的反射。這座100兆瓦熔鹽塔式光熱電站每年所生產(chǎn)的綠電可減排35萬噸二氧化碳。

2024年1月21日在甘肅省敦煌市拍攝的敦煌首航高科10兆瓦熔鹽塔式光熱電站。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馬希平 攝
電站負(fù)責(zé)人劉福國說,全球范圍內(nèi)的光熱發(fā)電仍處于多技術(shù)并存的示范發(fā)展階段,河西走廊上的這項(xiàng)探索,為推廣太陽能光熱發(fā)電提供了樣本。
面對全人類的共同課題——能源可持續(xù)開發(fā)問題,河西走廊在近十年間,持續(xù)貢獻(xiàn)著各類解決方案。這里的新能源技術(shù)和產(chǎn)品不斷走向世界。
2023年10月16日,遠(yuǎn)在哈薩克斯坦多斯特克的50兆瓦風(fēng)電項(xiàng)目正式并網(wǎng)。建設(shè)方介紹,電站并網(wǎng)后每年將為當(dāng)?shù)貛?.3億度清潔電力,緩解哈薩克斯坦東南部電力供應(yīng)緊張問題。
位于嘉峪關(guān)市的酒鋼集團(tuán)公司是該項(xiàng)目風(fēng)機(jī)塔架訂單的承接方。企業(yè)從生產(chǎn)、包裝、運(yùn)輸?shù)确矫鏋榭蛻袅可矶ㄖ品桨福f(xié)調(diào)技術(shù)人員遠(yuǎn)赴哈薩克斯坦,提供技術(shù)指導(dǎo)和解決方案。
從嘉峪關(guān)一路向東,就來到了寓意漢代“武功軍威”的城市——武威。這座扼守絲路樞紐的歷史文化名城,正躍馬揚(yáng)鞭,奔騰而來。
2014年,武威建成國際陸港,以“天馬”命名的中歐班列由此開出,裝載著西北地區(qū)的工業(yè)產(chǎn)品、特色農(nóng)產(chǎn)品運(yùn)往哈薩克斯坦、德國等中亞和歐洲國家。俄羅斯木材、中亞小麥搭乘返程“天馬”運(yùn)回國內(nèi)。
走進(jìn)武威國際陸港,塔吊聳立、叉車穿梭;木材產(chǎn)業(yè)園區(qū)車間里,木材滿倉,機(jī)器轟鳴,工人們正在加工一批自新西蘭進(jìn)口的木材。
幾個(gè)月前,這批木材搭乘輪船從新西蘭吉斯伯恩港出發(fā),越過茫茫大洋,歷時(shí)20多天,到達(dá)山東日照港,卸船通關(guān)后,又經(jīng)鐵路專用線裝車,運(yùn)至武威鐵路國際集裝箱場站,之后被加工成各類木制品進(jìn)入千家萬戶。至此,進(jìn)口原木完成了一趟新絲路之旅。
跨越山海,經(jīng)貿(mào)互利。眼前熱火朝天的景象,正如古絲路上川流不息的千年駝隊(duì),充滿生機(jī)與活力。河西走廊這條連通中外的金色紐帶,正以嶄新的姿態(tài)向世界敞開大門,世界也報(bào)以熱情回應(yīng)。
連心橋:互學(xué)互鑒的友誼廊道
駐足有著“萬神殿”之稱的莫高窟第285窟,壁畫上能看到來自印度的飛天,道教的朱雀、玄武,以及中國古代神話中的伏羲、女媧、雷公等形象。
小小斗室里,不同宗教共容一窟,東西方諸神同處一地。文明的碰撞交融孕育出了盛大輝煌、流傳千年的文化奇跡,其中的包容開放之姿更是令人驚嘆。
不難想象,兩千多年前,絲路重鎮(zhèn)敦煌是如何張開雙臂歡迎沿著河西走廊踏雪翻山而來的萬國來賓。文明的因子在歷史長河中漂流,在往來互通間生根發(fā)芽,在新時(shí)代通過更多樣的方式開出錦簇花團(tuán)。
敦煌漢簡、土庫曼斯坦樂器、巴基斯坦犍陀羅雕塑……2023年9月,在第六屆敦煌文博會(huì)上,來自20多個(gè)國家和地區(qū)的10萬件展品呈現(xiàn)了不同文明的傳統(tǒng)和藝術(shù),把人們帶入絲路歷史的時(shí)空隧道。

2023年9月6日,與會(huì)嘉賓在第六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huì)上參觀。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馬希平 攝
“我們的生活之所以豐富多彩,得益于文化的交流交匯。”甘肅政法大學(xué)教授奧莉婭·普隆金娜說。16年前,她在家鄉(xiāng)俄羅斯奔薩市觀看了中國舞蹈節(jié)目《千手觀音》,從此愛上了敦煌文化,如今她已成為敦煌文化的研究者。像她一樣,被敦煌文化吸引的外國學(xué)者越來越多,他們?yōu)橹型馕幕涣鞯墓适略鎏砹诵碌淖⒛_。
20世紀(jì)60年代,莫高窟迎來捷克斯洛伐克文保專家的現(xiàn)場授學(xué),由此開啟了敦煌文保技術(shù)的國際合作之路。其中,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hù)研究所的合作持續(xù)30多年,已成為我國文化遺產(chǎn)領(lǐng)域國際合作的典范。雙方合作完成修復(fù)莫高窟第85窟,探索文物保護(hù)流程,直接推動(dòng)了行業(yè)標(biāo)準(zhǔn)——《中國文物古跡保護(hù)準(zhǔn)則》的出臺。
與此同時(shí),敦煌研究院也與日本的東京藝術(shù)大學(xué)、東京文化財(cái)研究所、大阪大學(xué)及美國的西北大學(xué)等機(jī)構(gòu)開展廣泛合作。
受益于國際合作,敦煌文物保護(hù)事業(yè)不斷加速、人才不斷匯集,從過去的跟跑變?yōu)槿缃竦牟⑴堋㈩I(lǐng)跑,從過去的接受幫助變?yōu)榛W(xué)互鑒、共同進(jìn)步,壁畫、土遺址等保護(hù)技術(shù)已達(dá)到國際領(lǐng)先水平。
進(jìn)入新時(shí)代,尤其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敦煌研究院專家多次前往伊朗、阿富汗、烏茲別克斯坦等國,開展絲綢之路古遺址的考察和交流。通過聯(lián)合考古等形式,敦煌文物保護(hù)技術(shù)逐步走向吉爾吉斯斯坦等共建“一帶一路”國家。
文明交融是最美好的相遇。從古到今,河西走廊猶如一個(gè)大舞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因?yàn)槊\(yùn)與共的使命與責(zé)任,從不同地方來到這里。
在以山丹軍馬場聞名的山丹縣城,有兩位用外國人命名的街道:艾黎大道和何克路。
當(dāng)?shù)厝颂咸喜唤^地講出這兩條路的緣起:這是為了紀(jì)念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和英國友人喬治·何克在1942年創(chuàng)辦了山丹培黎學(xué)校。他們帶來了先進(jìn)的工農(nóng)業(yè)技術(shù),在河西走廊播撒下了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的種子。如今,這粒種子長成了參天大樹。
距離山丹培黎學(xué)校不遠(yuǎn)處,一所嶄新的培黎職業(yè)學(xué)院拔地而起。新學(xué)校將多年以來從國際教育合作中積蓄的營養(yǎng),轉(zhuǎn)化為向外輸送的能量,搭建起面向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職業(yè)技術(shù)培訓(xùn)的橋梁。

2024年1月23日拍攝的甘肅省張掖市山丹縣培黎職業(yè)學(xué)院。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張睿 攝
2024年秋天,首批巴基斯坦留學(xué)生將來到這里,學(xué)習(xí)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等實(shí)用技術(shù)。“在這里,巴基斯坦青年學(xué)子可以開啟新的旅程,在與中國學(xué)子的交流中成長、進(jìn)步。”巴基斯坦籍教師沙凱爾·杰米說。
杰米已在培黎職業(yè)學(xué)院任教兩年。他暢想著這些學(xué)子畢業(yè)后的無限潛能,或留在中國深造、或入職中資企業(yè)、或回國創(chuàng)業(yè)……中外文化交流與碰撞,正以新面貌為彼此提供更多價(jià)值。
在武威市區(qū)中心繁華的街道里,坐落著安靜祥和的鳩摩羅什寺。相傳這里曾是西域高僧鳩摩羅什的駐錫弘法之處。置身其中,八角十二層的佛塔巍峨莊嚴(yán),塔身懸掛的金鈴隨風(fēng)輕擺。
1600多年前,這位高僧踏上佛教東傳的要道河西走廊,客居武威17年,潛心學(xué)習(xí)中原文化,通過譯經(jīng)講經(jīng)推動(dòng)古老的華夏文明與古印度文明有機(jī)交融。
斯人已逝,而他所翻譯的典籍一直被沿用,其影響范圍早已遠(yuǎn)遠(yuǎn)超出河西走廊的自然地理界限。在這條他行走過的通道里,人與人的交流合作依然經(jīng)緯交織。

2023年6月1日,工人在武威市涼州區(qū)九墩灘光伏治沙示范園區(qū)管護(hù)噴灌管道。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馬希平 攝
離開鳩摩羅什寺,出城后一路向東,70多公里外的騰格里沙漠邊緣,數(shù)十名年齡、膚色各異的學(xué)員正在甘肅省治沙研究所科研人員的指導(dǎo)下學(xué)習(xí)壓麥草方格。聽著科研人員的介紹,他們在筆記本上用各自的語言記下關(guān)鍵步驟。
長久以來,河西走廊一直是我國北方防沙帶的中心地帶,這里的人們一直在尋求與沙漠的共生之道。他們的經(jīng)驗(yàn)已經(jīng)走出河西走廊,惠及飽受沙患的國家和地區(qū)。
來自納米比亞的農(nóng)業(yè)科技官員艾琳娜跨越一萬多公里、經(jīng)歷十幾個(gè)小時(shí)的飛行,只為學(xué)到有用的治沙方法。在她寫滿了要點(diǎn)的筆記本上,記者看到,她還專門手繪了麥草沙障的制作流程:先開槽,再覆草,麥草入沙10厘米,露出20至30厘米……
“改善生態(tài)環(huán)境關(guān)乎全人類,河西走廊的治沙實(shí)踐,為全球荒漠化治理樹立了標(biāo)桿。”艾琳娜說。
行道有盡,紀(jì)行未止。這條通道承載著人們對于詩意與遠(yuǎn)方的熱情追求,連接起跨越山海的相知相往,文明交流與融合的故事也將在這里延綿不絕。 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姜偉超 賈釗 張文靜 任延昕 郎兵兵
(責(zé)任編輯: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