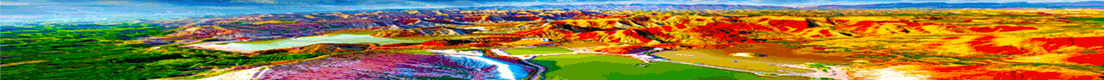他們來自異鄉(xiāng),可能帶著一身土氣,或者操著一口鄉(xiāng)音;他們活躍在城市所有能看見的空間里,保姆、保安、建筑工、推銷員、營業(yè)員,甚至還有取得一些成就的公司白領(lǐng),他們都懷揣著一個(gè)扎根城市安家的夢想,希望在這里實(shí)現(xiàn)人生價(jià)值;他們樂觀、自信、勤奮,渴望融入城市,渴望收獲愛情,重視社會(huì)保障……他們中的許多人正逐漸褪去鄉(xiāng)村氣息,從外表到思維以及知識(shí)架構(gòu)、生活習(xí)慣都在悄然發(fā)生著變化,鄉(xiāng)村的記憶正在城市生活中變得模糊……
夢想和現(xiàn)實(shí)只有一線之隔,他們?cè)谂蛨?jiān)持中逾越,相信在未來的某一天,他們無須再仰望城市。記者 沙莎 劉婷
城市生活
模糊了家鄉(xiāng)的記憶
被采訪人:小西(化名)
年齡:27歲
職業(yè):白領(lǐng)
27歲的小西在蘭州秀川一家私企上班,她的工作是法律顧問。淡淡的妝容,一身干練的職業(yè)裝,儼然標(biāo)準(zhǔn)白領(lǐng)麗人。和人聊天,小西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似乎早已沒有了小鎮(zhèn)姑娘的影子。小西的家鄉(xiāng)在距離蘭州不遠(yuǎn)的一個(gè)小鎮(zhèn),盡管算不上貧困,但依然不是小西想要的生活,于是她發(fā)奮學(xué)習(xí),以優(yōu)異的成績大學(xué)畢業(yè)后,又通過了司法考試,如愿以償?shù)卦谶@座城市扎了根。
和許多城市女孩一樣,小西與人交流也網(wǎng)絡(luò)化了,她的QQ掛在線上的時(shí)候多,有空時(shí)就和朋友們聊聊工作和生活的酸甜苦辣。KTV、酒吧,小西也常常會(huì)去,但總是感覺自己不適應(yīng)那種喧囂。
小西有著自己的“城市夢”:“我打算一直在城里住下去,現(xiàn)在我和男朋友存錢準(zhǔn)備買房子,然后,把戶口落在城市里。”
像小西一樣,如今在這座城市中,越來越多的異鄉(xiāng)打工者掙錢不僅是為糊口,而且還謀求更大發(fā)展;也不再是城里掙錢,然后回農(nóng)村生活。對(duì)他們而言,城市意味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意味著不一樣的前途和命運(yùn)。
小西告訴記者,今年春節(jié),她還是會(huì)回家,不管自己有多愛這個(gè)城市,可那個(gè)小鎮(zhèn)終究是自己出生和成長的地方,即便自己有一天扎根在這個(gè)城市,做了真正意義上的城里人,可小鎮(zhèn)依然是不能忘卻。“我想融入這個(gè)城市,也想方設(shè)法地不斷武裝自己,城市的生活有時(shí)會(huì)模糊了我對(duì)家鄉(xiāng)的記憶,但我永遠(yuǎn)也不會(huì)忘記我的小鎮(zhèn)。”
努力只為
那一盞為自己而亮的燈光
被采訪人:楊偉國
年齡:36歲
職業(yè):私營業(yè)主
如果把時(shí)間退回到20年前,若是村里有個(gè)人去城里工作,那是件多么榮耀的事啊。可在現(xiàn)如今的農(nóng)村,進(jìn)城工作早已成為一件司空見慣的事了。
楊偉國出生于1976年,他的家鄉(xiāng)在距離蘭州千里之外的福建省福州市閩侯縣青口鎮(zhèn)楊厝村,家鄉(xiāng)是個(gè)景色秀美的小山村,那里的人們淳樸善良,生活恬靜安逸、也并不貧困,可在楊偉國心中卻始終向往著大都市的生活。大學(xué)畢業(yè)后,他去了深圳,做了很多工作,也吃了不少苦,可依然無法消除內(nèi)心的孤獨(dú)感。“深圳始終是一座冰冷的城市,人們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快節(jié)奏的生活、工作的壓力時(shí)常讓我覺得透不過氣,就算我把出租的房子布置的再溫馨可還是絲毫找不到家的感覺。”深圳,在他的生命里,不過是一個(gè)臨時(shí)的驛站。
2003年,楊偉國和他的幾個(gè)老鄉(xiāng)一起逃離深圳,來到蘭州這座二線城市打拼,幾年的時(shí)間里,他做了很多事,也改變了很多,卻依然改變不了“異鄉(xiāng)人”的身份。如今他也算有了自己的生意,盡管這份事業(yè)并不算大,卻也可以讓他在這座城市衣食無憂。
離開家的日子長了,家鄉(xiāng)的輪廓似乎也漸漸模糊起來。楊偉國說,他們的家鄉(xiāng)如今早已改變了模樣,沒有了耕地,他的家也蓋起了4層小樓。村里的年輕人、中年人大多去了周圍或是更遠(yuǎn)的城市工作、安家,“可我們這些人都明白,無論我們走到哪里,根始終還在農(nóng)村。”
今年,楊偉國有了一個(gè)可愛的女兒,也和愛人終于在這座城市買下了第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房子臨河,風(fēng)景不錯(cuò),100多平米,盡管每月還要還四五千的房貸,但對(duì)于他們兩口子這是一個(gè)奮斗的動(dòng)力和目標(biāo)。和很多人一樣,他們的努力就是為了燈火通明的樓群里有一盞為自己亮起的燈光。
快到春節(jié)了,楊偉國開始盤算著新一年的生意怎樣發(fā)展,盤算著什么時(shí)候回家鄉(xiāng)看望年邁的父母,他還要在這個(gè)不屬于他的城市中繼續(xù)奔波,是為了當(dāng)初的夢想,還是為了現(xiàn)在的生存,已經(jīng)無暇去思考了。
要在城市里
找到我的白馬王子
被采訪人:王霞
年齡:23歲
職業(yè):手機(jī)銷售員
“回去,我沒有想過,回去干什么?我又不會(huì)種田耕地;除了打牌、看電視就沒其他娛樂,悶得慌。”王霞說得非常直白。
23歲的李霞是榆中人,在蘭州打拼多年,性格開朗、能說會(huì)道的她現(xiàn)在是一家通訊公司的手機(jī)銷售員,工作努力,每個(gè)月的業(yè)績都還不錯(cuò),收入也有3000元左右。多年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斷消解著小霞對(duì)家鄉(xiāng)存有的情感認(rèn)同和社會(huì)記憶,生活方式的巨大差異使她不再適應(yīng)農(nóng)村的生活方式。
生活和工作都還算如意的小霞,同樣有著對(duì)愛情的渴望。無論這種過程多么漫長,只要擁有一份美好的愛情,就會(huì)慰藉到她所經(jīng)歷的辛勞和卑微。小霞說,她的愛情可能不需要華美的衣裳和昂貴的首飾,而她需要的除了依靠,還有一份擔(dān)當(dāng)。“我要在這個(gè)城市里找到我的白馬王子,他可能也來自農(nóng)村,現(xiàn)在也在城市謀生,暫時(shí)也沒有發(fā)達(dá);現(xiàn)在已在城市扎根;或者他就是城市人,正在這座城市的某個(gè)角落里努力生活、工作,和我一樣期待愛情的降臨。”
其實(shí),在這個(gè)城市里還有很多外來務(wù)工者有著和小霞一樣純真的想法,愛情給了她們繼續(xù)留在城市的溫暖和力量,婚姻給了她們?cè)诔鞘猩l(fā)芽進(jìn)而枝繁葉茂的可能,哪怕她們都沒有多少錢,哪怕因?yàn)榉泵Φ墓ぷ饕惶於家姴坏矫妫呐禄楹笠患胰谝廊粩D在一間簡陋的、廉價(jià)的出租屋內(nèi)……即便是在這種生存狀態(tài)下,她們可以將城市的夢做得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只要有夢,她們的生活就會(huì)出現(xiàn)無限的可能。
想和城里人的
生活融在一起
被采訪人:楊文等
年齡:不詳
職業(yè):建筑工人
蘭州零下10攝氏度的天氣,冷風(fēng)吹得行人脖子直往衣領(lǐng)里縮。記者來到定西路一處建筑工地,建筑工人們正在忙著手頭的活,工地的門頭上掛著一條橫幅:抗嚴(yán)寒,戰(zhàn)低溫,力爭一月基礎(chǔ)完。
在距離門衛(wèi)室約50米遠(yuǎn)的地方,4名農(nóng)民工正在焊鋼筋。其中一名工人腳上穿著一雙解放鞋,頭上戴了一頂安全帽,里面套了一個(gè)毛線帽子。記者注意到,這名農(nóng)民工戴的手套早已看不出原形,手套指頭部分也已經(jīng)爛了。
在采訪中,記者看到兩名農(nóng)民工正在搬運(yùn)鋼筋。記者在一旁采訪不到5分鐘,已被冷風(fēng)吹得瑟瑟發(fā)抖了。當(dāng)記者問他們冷不冷時(shí),一名姓張的農(nóng)民工哈著氣:“活都干成這樣了,身上倒是不冷,只是手腳冰得很。”旁邊正在搬鋼筋的工人對(duì)記者說:“干這活,最費(fèi)的就是手套,搬運(yùn)鋼筋差不多三天就得磨爛一雙。”透過每一雙磨破的手套,記者看到了農(nóng)民工凍得通紅的手指。
接受記者采訪的這位師傅名叫楊文,他看上去身材高高大大的,皮膚有點(diǎn)黑,一看就是干活的一把好手。果然,楊文已經(jīng)在工地上干了十幾年。“十幾年建筑工人做下來,除了多賺錢,就是想把工程又快又好地完成。辛苦點(diǎn),但是工程做得好能拿獎(jiǎng),我們不能回家過年也值得。”在進(jìn)入工地前,楊文遞給我們幾頂安全帽,并叮囑要時(shí)刻注意安全。他說,“架子班”的主要工作是在工地上搭建和拆除腳手架,保障工程和維護(hù)安全。
當(dāng)我們看到他們正在搬運(yùn)鋼筋的工作時(shí),以為這應(yīng)該是很容易只需要有力氣就可以了,實(shí)際上遠(yuǎn)遠(yuǎn)比我們看到的要復(fù)雜得多。楊文告訴記者,這個(gè)工作危險(xiǎn)性很大,不能隨隨便便就讓人上腳手架,“一根鋼筋有幾十斤重呢,一不小心就會(huì)砸了腳,我們長期從事高空作業(yè),面對(duì)的危險(xiǎn)是常人不能想象的,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保護(hù)好自己、保護(hù)好身邊的人。”
工地上的活干起來乏味又枯燥,但容不得一絲馬虎。實(shí)在無聊乏力了,任行龍他們也會(huì)互相開開玩笑,放松一下。這個(gè)時(shí)候,單身的幾個(gè)小伙子就成了他們打趣的對(duì)象。“喲,小伙子,老婆本賺夠了吧?”楊文師傅擺著手套上的泥土笑著說道。
工人們有的時(shí)候也會(huì)互相之間聊聊天,說起最遺憾的事,楊文師傅說道,自己最大的遺
憾就是沒有時(shí)間陪伴兒女成長。“我們十幾年下來每天都是這樣,現(xiàn)在的條件好了,晚飯后就看看電視,和工友聊天打牌。”楊文笑得很滿足。
楊文的老家在武威的一個(gè)小縣城,今年45歲。去年,女兒考上了蘭州的一所大學(xué),而16歲的兒子仍在老家讀高中。“他們倆蠻聽話的,我雖然沒有時(shí)間陪他們,但好在他們很讓我們省心。”孩子們?cè)跅钗耐獬銎床珪r(shí)漸漸長大了,而作為父親的楊文卻沒有時(shí)間和他們一起經(jīng)歷分享成長中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
“已經(jīng)放假的兒子打算和老婆一起來蘭州看望我和女兒,妻子和孩子能陪在自己身邊,一起吃吃飯,聊聊天,一年辛苦就為了那么幾天。”說起就能見到的一雙兒女,楊文就忍不住笑了,他告訴記者,趁休息日該去看看年貨了。
現(xiàn)在,唯一讓他牽掛的是老家年邁的父母。“我去年春節(jié)就沒回,今年又回不了家,有些愧對(duì)父母親,他們都年近七十,幸好身體還不錯(cuò),挺想他們的。”過年沒回老家的楊文,想對(duì)父母說“新年快樂”,并且打算將攢了一年的工資寄給父母。
采訪中,不少農(nóng)民工向記者表達(dá)了自己對(duì)生活的愿望:“再苦再累咱不怕,只希望干活多掙點(diǎn)錢,能給家里人帶來更好的生活。”木工黃師傅告訴記者,馬上他就快攢夠錢夠一套小戶型的首付了。平日里下了班換掉工作服,也和工友去一些娛樂消費(fèi)場所唱唱歌吃吃飯,也想和城里人的生活融入在一起。
采訪手記
其實(shí),我們采訪到的這些人,不過是這座城市中一個(gè)再普通不過的人,故事甚至不具備任何典型,卻是成千上萬異鄉(xiāng)務(wù)工者的縮影。事實(shí)上,他們也正在融入到城市的人流中,用城市的思維方式思維,用城市的生活方式生活,用城市的審美方式審美,他們正一步步融入到城市人的行列中來。
我在想,每當(dāng)夜幕降臨的時(shí)候,這座城市里成千上萬的異鄉(xiāng)人,望著都市街頭閃爍的霓虹燈,望著漸漸亮起的高樓大廈里的通明燈火,或是路邊小屋里的昏黃顏色,在行色匆匆的路人當(dāng)中放緩腳步,在繁華喧囂的街頭駐足自己的身影,他們會(huì)不會(huì)突然覺得有一種不能融入的尷尬?但無論如何,在日復(fù)一日的勞動(dòng)中,在耳濡目染的氛圍中,在時(shí)時(shí)刻刻的近距離凝視中,他們的談吐、外貌乃至思想、生活狀況,都會(huì)被城市悄然同化。
城市打開了世界的窗口,也圓了那些睿智的異鄉(xiāng)務(wù)工者的夢,他們會(huì)在城市里發(fā)現(xiàn)讓生存變得更加豐富的可能和機(jī)會(huì)。也許他們會(huì)因?yàn)楸拔ⅲ瘸鞘腥烁庸摇R坏┯辛艘欢ǖ脑挤e累后,他們就會(huì)義無反顧地從臨時(shí)工、服務(wù)員這些安全又脆弱的“蛋殼”里跳出來,昂首闊步地走向更加艱險(xiǎn),同時(shí)也更加敞亮、更加自由的天地,開始真正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主,靠自己的努力贏取更多的財(cái)富,擠向更高的階層。事實(shí)上,不管他們從內(nèi)心里愿不愿意,他們已經(jīng)很難回到農(nóng)村那個(gè)貧窮落后、幾輩子人拼命想逃離的地方。他們的執(zhí)著和堅(jiān)持,注定了在未來的某一天,他們無需再仰望城市。
這種來自生命最本真的力量,無論你來自何方,也無論你操著什么樣的鄉(xiāng)音,毫無偏見地照耀著每一個(gè)人的青春夢想。除此之外,才是她們的思想、生活和審美觀念與城市女孩的逐漸趨同。
(責(zé)任編輯:鑫報(bào))